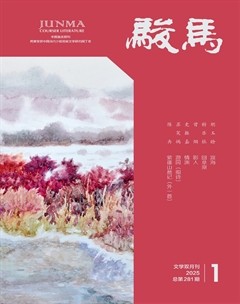乌琼(以下简称“乌”):《骏马》的前身《呼伦贝尔》期刊(1985年更名为《呼伦贝尔文学》,1989年更名为《骏马》)于1980年创刊,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创刊的背景吗?
刘迁(以下简称“刘”):要说《骏马》的创刊背景,第一是时代的大背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团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各族人民摆脱了束缚,思想解放了,就产生了强烈的阅读和述说的双重需求。因此,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纷问世。
时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的云照光同志,特别关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后简称“三少”民族)文学事业,对长时间没有出现代表人物深感遗憾。《骏马》就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由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发文批准创办的。可以说,《骏马》是时代的必然幸运儿。诚如时任呼伦贝尔盟宣传部长敖特根的发刊词所题——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并且,地区文学发展到了需要一个有担当平台出现的时期。虽然呼伦贝尔地区有着丰厚的多民族文化积淀,各地已出现虽为数不多,但也甚有影响的作家作者。他们亟须一个稳定的展示才华的舞台。恰在1979年上半年,在盟委的关怀下,呼伦贝尔盟召开了首次恢复文联建制的代表大会,原文联只有一人,设在教育局内。会议开得十分隆重,选举产生了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同时完成组建作协、美协、音协、舞协等专业协会并选举产生了负责人。蒙汉文《呼伦贝尔》两个文学期刊,酝酿已久,文联成立之时,即刻委派专人,将刊物组稿等工作着手实施,并确定了汉文《呼伦贝尔》基本任务,就是发现培养当地作家作者,尤其重点发现培养“三少”民族文学创作人才。
乌:文联初创时期,呼伦贝尔文学创作队伍在80年代伊始情况如何?经过十年的培养,有怎样的成长?到90年代作家队伍的整体样貌是怎样的?期刊主要承担的任务是什么?
刘:《骏马》出版发行前,可供文学作者发表作品的平台,只有正式出版发行的《呼伦贝尔日报》和《大兴安岭日报》两份报纸的副刊,一周一版是常态,由于版面局限,也不可能发大篇幅作品。这就束缚了小说创作。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的重要时期,文联成立之前,由盟文化局(创评科)与《呼伦贝尔日报》社共同发起一次促进文学创作的征文活动。汉文方面由我、郭纯和报社李鹰共同主持。针对小说创作是最大的短板,我们决心通过此次征文获得突破。所以,一直坚持,宁愿一再推迟发稿,以表明征文的目的和期待。终于等来一篇小说,立即作为征文第一篇作品在《呼伦贝尔日报》全文发表。虽听到有微辞,但我们仍表现出支持的决心,坚定推动短篇小说创作。此后不久,又发表了乌热尔图的《熊洞里的孩子》,打开了小说创作的局面。呼伦贝尔盟文联就是由原盟文化局副局长冯国仁率创评科为基础组建立起来的。所以,《骏马》从创刊开始就坚定组织和推动短篇小说创作。没有小说,是支撑不起一个文学期刊的,某种意义上则是地区文学现实的大缺憾。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78年《人民文学》要办一期少数民族专号,赵则训编辑直接来到海拉尔,经我们介绍,他去了敖鲁古雅,见到了乌热尔图。在那一期专号上发表了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这篇小说的发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标志着乌热尔图真正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以为,这也标志着呼伦贝尔文学告别了最初的寂寞,开启了大踏步向前的发展阶段。
呼伦贝尔文学发展步伐是极快的,这是时代的恩赐。我们编辑部清醒地认识到作者强烈的述说愿望和读者的阅读需求,便迅速地采取措施,目标明确,即探索并实践中篇小说创作。为此,大约是1983年春末夏初,编辑部在阿荣旗举办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为中篇小说创作思考提供可炊之“米”。于是,组织作者深入农村,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引发社会与人的最现实的变化,从而为中篇小说创作积累基础素材,争取实现再突破。出乎意料的是,通过这次活动,不仅促进了中篇小说的跃进,更催发了长篇小说的鲜花频放。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研讨会对呼伦贝尔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短、中、长篇小说全面鲜花绽放,由此开始成为常态。
经过主动组稿,于1983年第3期特别推出了“中长篇小说专辑”(长篇另论),集中发表了崔鹏、何德权、王常君、王高衡(兰英)和我的五篇中篇小说。据我所知,虽然崔鹏和王常君是老作家,但这五个中篇,都是作者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中篇。说到我自己,《一支古老的情歌》应该是第二个中篇,因为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新苑》在当年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迟到的婚礼》,时间稍早于《骏马》发表的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