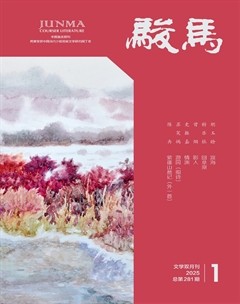《蛹归集》是渟文的第二本诗集,分为“物哀万象”“幽玄书房”“侘寂墨香”“心猿意马”等四辑,单从名字就可以管窥这本诗集的风格气象与精神内质,这也是诗集最大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全诗集弥漫着浓郁的物哀气象,这和诗人的留学日本经历以及积累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往更高处说,则是一种“物哀”的文化精神,其呈现是对诗人以及其诗从性格、日常生活、风格、内涵等多方面因素的萃取与升华,但这样的“物哀”实际又和日本文化中以往的物哀气象并不完全相同——在立足日本传统物哀精神气象的基础之上,实际可以看到的是,渟文诗中所反复涌现的“物哀”之质与文化精神是一种来自自身经验范围的现实化的物哀,即是说,这种“物哀”气象从日本以往的物哀传统的抽象层面脱离而出,进而更具象化地变现在诗人身上,那是个人性的、时代性的、日常生活性的,经验性的甚或是后现代之下的具体时代性“物哀”新诗,在诗中,这种独特的“物哀”气象正是在个人经验与遥远精神的双重构建之下呈现出来的。
一、万物显情与“物哀”精神
“物の哀れ”是常被提到和重视的美学概念,表示为物的哀婉或物的凄凉,这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在日本传统中,讲求淡泊、反对浮华,日本传统上流社会精英阶层,将追求自然与精神财富看作更高尚且值得尊重的人格。因此,当物品逐渐衰败、损坏,失去了原有的荣光和希望时,才会显为动人,从而引发很特别的审美情绪。
虽则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化语境的变化,“物哀”一词也跟着变化,并没有一个四海皆准的定义与说法,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会形成不同的物哀审美,大范围来说,所谓“物哀”即人的情绪与感官对世界与万物做出观察、体验与赋值的人性化情感显化,用中国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但人之一情又是包罗万象且各不相同的,在渟文的诗中,其“物哀”的特点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人与万物亲近、感伤以及最终到人生思索与哲学探讨的层面,总体而言,走的是一条“哀伤化”的路子(风格),这当然不是诗人刻意如此,而是诗人本身性格与生活经历叠加的必然结果——渟文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海归,研究生学历,在日本,他耳濡目染地学习了很多日本的文化,“物哀”作为日本绕不过去的美学概念能给渟文很大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不必说跟着其导师桥本雄一学者继续深造,使得渟文对日本以及物哀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加之渟文本身单纯、敏感、多愁与善良的性格,在“物哀”的层次上更倾向(契合)于“哀伤”也是情理当中的。
渟文诗中,多的是与万物彼此赋值的情思,如《寻香》《雨+雪=?》《雪花飘出冬的思绪》《一条热闹的河》等,万物是热闹的,诗人是孤独的,在孤独中以“万物”来显情,更体现出近乎悲怆的“物哀”气象来,这也是诗人将第一辑谓之“物哀万象”的原因,而且还将之扩大的,万物以及人在万物当中的处境,也可以叫作“浮世”——世界虚实不定,人生如一叶飘零,孤苦无依,这样的浮世也正是渟文诗中物哀的起点,人在浮世中,毕竟渺小、卑微得可怜,而浮世如亘古的时间之河一样永不停息,世事多艰难,心绪常起伏:诗人在《进城》中写道:“经常更换的工牌栓起你我/餐桌闲聊和游戏变为外套”,渟文将世间万象的忧苦全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放进诗行,这本身就需要对生活有更深层次的感触和思考,但又不一味沉迷于这种思考所带来的感伤,而是恰当走出来,以一种近乎乐观的心态对悲观的世象作出自己的反抗,从而将表面的“物哀”气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哀而不伤;在《万物透影》里写:“天外昏暗,从头到尾/一个生日,只想躺着/偶尔计算剩余的工作/我与外面的黄沙,相识甚久”。窗外风沙呼啸,天地一片昏暗,而这天是诗人的生日,不过这样的生日与往常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庆祝,诗人一个人孤零零在家躺着,还得考虑工作的事情,无声的感伤就此萦绕,而“我与外面的黄沙,相识甚久”这句诗无疑是平常的震撼,将诗人的孤独、感伤以及哀愁通过一种平常式的聊天语句展现得淋漓尽致,更展现其诗犹如大道低回般的“物哀”之象来。
这是一种极高的物哀境界,诚如前面所说的“哀而不伤”,诗人并不是一味在抱怨社会以及感时伤怀,这是最低级的物哀,而诗人基于此但更高于此,体现的是一种在感伤之后又归于平静和坦然并以轻松且近乎戏谑的口吻表达出来“物哀”,这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返璞归真的心境,“黄沙伴随着歌声——太多,却不够重”(《万物透影》)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黄沙”是感伤的,“歌声”则是反抗,将两者结合却是一种悟透人生的中庸选择,不偏不倚,不过哀,也不狂欢,理解了诗人的真实心境,就不难理解后面那句“太多,却不够重”了:人世纷繁,世事复杂,但诗人已经看透,不执着,不留恋,他早已回归自我,只是渺茫天地一沙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