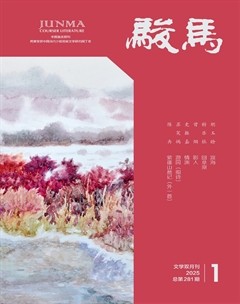山中寻茶
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喝茶,是喝茉莉花茶,那年在苏州拙政园,6元买回一大包茉莉花瓣,开始了一个19岁少年的风雅喝茶。
从前在小城的茶店买茶,卖茶师傅从玻璃罐中,小心翼翼称取二两珠兰,用大拇指和食指拈一小撮,包在一个纸袋里,我怀揣着茶叶带回家,烹水泡茶,杯中放几瓣茉莉花。其实是那时不懂茶,放入花瓣,冲淡了茶香,把茶的意境给破坏了。
我的家乡不产茶,产茶的地方,对一个爱饮茶的人来说,是多么幸福的情感滋养。
南方有嘉木,我到江南小镇访茶,看到那些卖茶人坐在半明半暗的茶铺里,坐在茶香灯影之中。那里街道狭窄,灯火可亲,我带走一包茶叶,也带走一片芬芳心情。
我喜欢用玻璃杯喝茶,杯子透明,是为了将杯中的茶看得真切,就像喜欢看容颜清丽的女子。
早年,喝过维扬蜀岗茶、金陵雨花茶、宜兴阳羡、黄山毛峰……我对茶叶从不挑剔。
茶是山中的君子和隐士。这些年,我到茶的故乡去,在“钟山只隔几重山”的镇江山间问茶,在宜兴的碧碧茶坞里买茶,在安吉的青青竹林边寻找白茶,在武夷山的岩壁上仰望大红袍,在厦门的榕树下品铁观音……又到过红茶的老家——安徽祁门,去寻访红茶。红茶汤色红艳明亮,是真正的茶色。许多年前,我戴茶色眼镜,现在想来这不就是茶汤的颜色?茶入口醇香,有一股松脂的香气,叶片放多了,微苦。茶叶是一截一截剪碎了的条索,紧缩苗细。不知道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茶,是不是对茶叶的尊重?一寸一寸的尊重,来自茶农和喝茶人细微爱慕的内心。有个性的茶,坚守的是自己内心的底色,一种独特的茶色。我本来是不喝红茶的,去了祁门,就喜欢上了红茶。
从牯牛降下来,在祁门与石台县交界的路边买了一袋红茶。我觉得红茶耐喝,撮一小撮乌润红茶,把它放在平时常喝的玻璃茶杯里,深深的茶色,铺张开来。一般的绿茶,泡上两三杯,茶味和茶汤的颜色就淡了,而红茶可以续泡。绿茶大概是给男人喝的,碧绿的茶汤,有一股茶中的霸气;红茶适合女人喝,茶色恬静,滋养容颜。
我还在超市里买过茶枕,回来掀开一看,发现里面其实是一枕袋红茶。每天晚上,头落在枕上睡觉、想事,有一股淡淡的,熨帖皮肤的清香。
有一年去皖南,在山中见一老者,提半旧竹篮,坐在石阶上卖茶。同行的人买了两袋。刚开始,不知道是野茶。那个朋友问卖茶的老头,对方说是野茶,20元一包,后来又让价,35元两包。别人要买茶时,老头拍着手上的灰尘,摇摇手,说:“没得了。”
老头卖的野茶,大概是他自己在山上采来的。后来,我在石台县城的一家小店里见到野茶,价格比山里老头手上的要高出许多。
野茶野在哪儿?大概是山野里零星地天然生长的茶。茶叶的品相看上去,当然没有礼仪小姐那么迎人,也没有一般绿条一层浅浅的绒毛,叶片壮厚,叶纹细腻,卷曲着,显得清纯,细细长长。
在山里和县城错过的野茶,自然是买不到了。我觉得好茶是寻出来的,山中寻茶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在微信上,岭南书友闻知我喜欢茶叶,欲寄赠我当地的名产“鸭屎香”,被我婉拒,我喜欢身临其境,在山中青青茶园间寻茶时的那么一种心情和氛围。
当然,我极喜欢猴魁。曾在太平、黟县等地打探寻访。想想猴坑那样的地名,人未去山中,倒是变得风雅起来,于是杯中茶,也有几许山野清气。
雨天留客闲饮茶
落雨天,最惬意的事,莫过于留客闲饮茶。
客人来访,正欲抽身离开,偏偏雨来了。雨丝一阵紧似一阵,客人走不了了,不如坐下来,聊天闲饮茶。
这是江南梅雨天常有的事。留客闲饮茶,宜一攀满凌霄花的草庐。宾主列坐,案几上,几盅茶盏,丝丝微漾,仙气袅袅。
喝茶时,不慌不忙;主人与客人晤谈,亦不紧不慢。
这样的雨天,絮叨絮叨,谈的都是家常话、应景话。要紧的话、正式的话,已经说过,现在下雨,雨滴打在屋顶簌簌有声。这时俩人说话,雨大时,说话声被雨声淹没。
我的眼前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两人坐在室内饮茶,外面飘着晶亮的雨丝,端坐者神态从容笃定,表情平淡。
这是一幅古画。画中有两个雨天喝茶的人,离我很远,大约是在宋朝。
闲饮茶,它的传神之处在一个“闲”字。人闲,听雨声;人闲,闻鸟鸣;人闲,品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