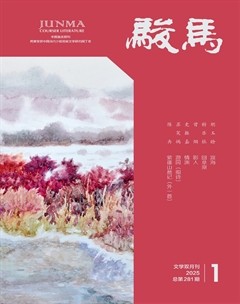父亲丢了。
周河是在上午十点半才察觉到这一点的。熬夜喝酒让他身体发虚,无法从困倦中抽身。他抬起头,眯着眼艰难地环视四周,许久也没想起昨夜发生了什么。这不能全怪他,每家酒吧白天的时候都和深夜大相径庭。
酒吧老板端来一杯冰水:“醒醒酒。昨天晚上喝断片儿了吧。”
周河端起冰水一饮而尽,冰冷的刺痛感从喉咙直插胸腹,确实清醒了不少。
“我一直趴着睡到现在?”
老板点点头:“是。反正店里也没客人了,随你睡。”
周河的记忆像拼图般被安上了一小块——这家酒吧要关门歇业了。
“我昨夜一个人来的?”
老板摇摇头:“你和一个老头一块来的。你说他是你爸,他说他不认识你。”
“老头呢?”
“不知道。早上就没影了。”
周河冲出酒吧,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眼。“云阁”两个字有些褪色了,旁边的氖气管霓虹灯被盛夏炽烈的阳光炙烤,反射出刺眼的红光,像破碎得几近模糊的八十年代。
那张收据是他偶然发现的。昨天周河叼着烟收拾杂物的时候,老头正坐在床边发呆,晶莹的口涎从他唇边流出,丝线般拉扯到裤腿上。周河不准备帮老头擦,他甚至对这种现状感到满意——你往裤子上流涎水,我往地板上掉烟灰,咱爷俩谁也别嫌谁脏。
往前推三十年,整个棉纺厂家属院,没人不认识周河他爸。话少,倔,但是个体面人。周河小时候就听过父亲的光荣事迹:为了追周河他妈,父亲天天往棉纺厂溜达,门卫以为他是来踩点儿的扒手,虎着脸咋呼了几句,父亲压根没搭理他。门卫也是暴脾气,袖子一撸冲到门外,结果被父亲一个趟地拐撂在地上,这一手力道控制得极好,人被摔得狼狈,但绝不会受伤。门卫看出父亲是个练家子,过了两天拎了一挂猪头肉上门主动道歉,想学这手撂跤的本事。父亲把动作要领细细讲解,送门卫离开时把那挂猪头肉原封退还,拍拍门卫的肩膀:“下回跟人开口时,说人话,别耍横。学会这个,比撂跤强。”
父亲那手撂跤的本事没在周河身上用过。实际上也不需要,只要一巴掌扇下去就够了。母亲在周河六岁那年死于心梗,家里只剩两个男人,日子变得肉眼可见的糙了起来。周河依然按时上学,看电视,出去疯跑,但他察觉出家里少了什么,原本坚硬冷漠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房门将家和外界分割成两部分,门外喧闹如常,门内连空气都凝滞成了某种艰涩的固体。周河逐渐意识到母亲在世时充当了何等重要的缓冲剂,当家里只剩两个男人时,直来直往的碰撞与较量已然无可避免。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周河忘了在卷子上写名字,最终成为全年级唯一一个没成绩的孩子。他仍清楚记得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挨父亲巴掌的一瞬间,仿佛一块烙铁轰击而来,全世界在那一秒压缩成一道黑色细线。失去意识前的一刹那,他清晰地听到挤在门口看热闹的同学们发出的惊呼和哄笑。周河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家里的床上,父亲已经把身上的工装熨得一丝不苟准备去上班,只简单地甩下一句:“锅里有粥,喝完了做作业。”平静得仿佛一切如常。
周河一直认定自己的离开是个必然结局。倒不是因为害怕挨打,实际上他从小到大挨了无数次巴掌,早已接近麻木。电视上播香港武侠剧时,周河甚至含着泪难过了很久,幻想自己并非亲生,而是被仇人收养的悲惨主角。但青春期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这种假定的界限并不存在——他无力抵抗DNA,父亲的血脉在他体内开始越来越多地体现,他变得沉默、强硬、倔强,处事风格变得和父亲越来越相似,而他对此极其抗拒,这种抗拒最终演变为某种决心,成为他离开的理由。他决定南下打工的那天晚上,父亲炖了一整锅鲇鱼茄子,拍了盘黄瓜,还去买了蒜肠和熏鸡,桌上甚至不能再多放下一只碗。周河落座的时候,父亲把那瓶珍藏了十年的老西凤拿出来,郑重地给自己和周河各倒满一杯。父子对坐,父亲如往常般腰背笔直,身形如山。周河握着酒杯的手心冒了汗,他突然很期待父亲说点什么。半晌,父亲问:“真要走?”周河答:“定了。”这两句话成为当晚父子二人的唯一交流。沉默片刻后,父亲将整杯白酒一饮而尽,周河一仰脖也干了。那天晚上,滨县下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夜幕被雪花割裂得斑驳细碎,仿佛老式照片上抹不去的灰色噪点。
酒吧老板追出门,把一个信封递给周河。
“这是什么?”
老板大笑:“看来是真喝断片了。这是你昨晚要的照片,我找着了。”
周河接过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胶片机拍的,塑封上印着“2014年2月4号,云阁留念”。照片里是他和父亲并排坐在一个满是便利贴的墙边,光线有点暗,俩人隔着一小段距离,拘谨得不像父子。看到这张照片的瞬间,周河的记忆拼图又被安上了一小块,他想起了昨晚带父亲来这家酒吧的原因。
2014年的春节,周河原本没打算回滨县过。彼时他正被工作逼得焦头烂额,眼看连房租也要无力为继。必须承认的是,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倔强性格,让周河扛过了许多难关,这次他也不准备对任何人开口求助。从周河外出打工的那天算起,父子俩通话的次数不超过一只手,内容也仅仅局限在极其有限的几个话题内。周河能隐约感觉到父亲想跟自己多聊聊,但每次二人开口时,这种本来明确的目标就会隐匿不见,仿佛穿行于大雾之中,满目所及只有困惑和误解。某天周河带了六两散白回到出租屋,突发奇想地拿出两个纸杯各倒了酒,对着墙壁发问:“你为啥这么拧巴?”墙壁没有回答。周河又问:“你是我爸,还是我仇人?”墙壁依然沉默。周河把两只纸杯里的散白一饮而尽,点点头,“你跟我爸一模一样。”
腊月二十八那天,周河手机来了电话,是父亲打的。多年父子,周河深知父亲性格,赶紧接了:“出啥事了?伤着了?病了?”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父亲的声音传来:“没出事。”
“那咋来电话了。”
“过年了。”
周河甚至能想象得出,如果母亲还活着,这通电话会在怎样的嘘寒问暖中进行——你那里冷不?年货备好了吗?还回来不?跟谁一块过年啊?
然而都没有。除了简单到极致的“过年了”,父亲再无言语。话筒那边传来极其细微的呼吸停顿,像是某种被刻意掩盖的欲言又止。沉默许久,父亲的声音再次传来:“我挺好的。年菜刚炸好了一盆,花生油炸的,香。你缺钱言语一声。就这么着吧。”
挂了电话,周河立刻订了回滨县的车票。火车摇晃着驶向地平线,周河的心反而愈发平静。他不知自己为何要回家,但能感觉出这是一种必然的责任。周河仍能隐约记起关于那年春节的些许细节:自己推开家门时父亲惊愕的眼神,当晚的父子对酌,鞭炮燃尽后的零碎纸屑。父亲仍旧话少,但话里话外已经少见对周河的不满。第二天周河醒来时,隐约听见父亲在客厅打电话,听那意思是崔叔拉他去打麻将。父亲义正辞严地拒绝:“我哪脱得开身?又不是一个人过年,孩子回来了,一堆活等着干呢,过了年再说吧。”
大年初三,周河骑电动车带父亲出门,骑到滨海路突然捏闸停车,指着路边刚开业的一家小店:“爸,你咋还瞒着我开店呐。”小店名叫云阁,和父亲的名字一样。父亲被寒风冻得鼻头通红,听到这个拙劣的笑话,他难得咧开嘴笑了一下:“进去看看。”父子俩进了店,第一眼就看见满墙的便利贴,上面写满了不同的寄语,大多是对未来的憧憬,有些还在旁边附了照片。店主是个小青年,凑过来解释:“我们这儿是个时光驿站,你们可以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或者拍张照片,十年后寄给你们。”周河笑了笑转身就往外走,他知道父亲这辈子没拍过几张照。走了两步觉得不对,回头一看,父亲站在原地没动。
“有想法?”
父亲看着满墙的便利贴,许久之后点点头,“要不,拍张照片吧。”
一种陌生而强烈的寂灭感将周河包围。这一瞬间,他陡然意识到,过去的某种坚固正在坍塌。
爷俩拍完照出来的时候,外面又下起了雪。尽管是沿海地带,但滨县仍然兼具了北方城市的粗粝,夹杂着雪粒的寒风吹得人脸颊生疼。父亲很认真地把收据折好,放进钱包夹层里:“等十年后来取。算是留个念想。”周河给他整好领口:“十年,这店早他妈没了,上哪取照片去,就当买个乐了。”父亲叹了口气:“你还年轻,不知道岁数大了之后时间过得多快。十年,眨眨眼就过去了。”
这一幕清晰地刻在了周河脑子里。
昨天他叼着烟收拾杂物的时候,没指望能找到什么值钱东西。老头曾经是个讲究人,家里的大小杂物都收拾得妥当整齐,得病之后就垮了,旧袜子、火柴盒、自来水催费单随手乱塞,抽屉里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周河翻到省人民医院的诊断单,把上面的“阿尔兹海默症”几个字又看了几遍,揉成一团扔到了垃圾桶里。又翻到父亲的技工证,封皮褪色成了不均匀的暗红色,像逐渐消逝的潮汐。再往下翻,一个叠得工工整整的小布袋子,打开,里面是工资存折、房产证,还有夹在中间的一张收据。周河掏出手机查了下地图,云阁这家店居然还在。他试着打了个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老板:“原来那家时光驿站早就倒闭了,现在的云阁是家酒吧。不过,早些年客人们留下的那些照片都还在,他可以帮着翻翻看,不保证能找着。”挂电话前,老板又说:“酒吧明天也要关门了。你们俩今儿晚上来吧。酒管够,不收钱。”
手机响了。周河站在酒吧门口发蒙,太阳晒得他有些眩晕,旧照片反射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昨夜残留的酒精让他反应迟钝。铃声响到最后一下他才接了起来:“喂,哪位?”电话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小河?是小河不?”周河愣了一下:“崔叔?”电话那头传来爽朗大笑:“问了一大圈,可算问出你手机号了。刚才我听老于头说,早上遛弯的时候看见你爸了,我琢磨着你们爷俩都搬家十几年了,又听说你爸有点那个什么,脑萎缩那个病,别再是一个人出门走丢了,所以得问你一句。”
去崔叔家的时候,周河不得不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摘了头盔拿出手机。他本不想查地图——他在棉纺厂家属院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按说应该熟得闭着眼都能找到。但滨县的变化太大,交错的小巷和陌生的街道让他失去了所有把握。这座城市如同父亲一样,已经和周河有了微妙的疏离感。
骑到西河下游的时候,周河放慢了车速。他看见那座斑驳的小石桥,河边的桦树林,以及地势低洼的小河湾。这些熟悉的景色仿佛暗室里的胶片,久远模糊的影像渐渐清晰,灰白的画面被重新浸润出色彩。
从周河记事起,西河就是他常来的地方。西河下游离棉纺厂家属院很近,层叠的砂岩将河道折出一道绵长的弯,慢慢攒成一汪深潭。每到周末,父亲总会提着马扎来这里看人钓鱼,周河就跟在他屁股后头乱晃,有时候去河边玩沙子,有时候钻到旁边的桦树林里捡蝉蜕。那时的他还小,日子平静又漫长得要命,父亲的沉默还并不令人窒息。那天夕阳西下,父子二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回家,在小石桥边看见一堆尚未烧尽的纸钱。余烬明灭不定,泛着幽暗的光。周河问:“这是啥。”父亲说:“这是座桥,跟小石桥一样。活着的人站在这头,没了的人站在那头,想对方了,就烧纸钱搭个桥,往那边看看。”周河看着那堆纸钱,胸膛里生出一股莫名的哀愁。他拉着父亲的袖口,说:“以后你要是死了,我也烧纸去看你。你要是也回来看我了,就用风在周围打个旋儿。”父亲往地上啐了口:“脑子抽了,咒你爸。”走了两步又回头,在周河脑袋上使劲儿摸了两把。
来到家属院已经是十一点半了。崔叔等在大门口,他比周河印象中老了许多,头顶只剩了稀疏的白发。周河把摩托车停好,拎下刚才从小超市里买的一箱奶和一兜水果,任凭崔叔怎么推脱,最终还是硬塞了过去。崔叔点点头:“行,你这孩子在外头没白混。跟你爸一样,讲究人。”
“叔,啥时候看见的我爸?”
“老于头说是早上八点多。”
“我爸没说啥?”
“说了,他还跟老于头聊了几句,跟没事儿人一样,就是聊的内容不对劲儿,他不记得自己早就从这儿搬走了。”
“是,他最近糊涂得厉害,都不认人了。昨夜我带他出门,他跟人酒吧老板说不认识我。”
“老于头是不知道你爸有这病。他要是知道,咋说也不能让你爸走了。”
“我爸没说他去哪儿?”
“说了。他走得急,边走边跟老于头撂了句话,说他去接你放学。”
周河生出一股疲惫感。他别无选择,只能重新骑上摩托,往二中的方向驶去。周河曾在那里度过初中时光,干瘪又痛苦的三年。
当摩托车在二中门口停下的时候,周河隐约有了种预感,父亲不在这儿。自己一路追行,追赶的似乎只是过往的影子,若有似无,无法触碰。正赶上中午放学,学生们从大门口蜂拥而出,一张张年轻稚嫩的脸从周河身旁闪过,像悄无声息从生活中流逝的每一秒。嬉闹拥挤的人群流到马路对面,学生们在一辆辆停下的汽车旁穿行而过,如同潮水拍打礁石。周河曾是这潮水中的一员,他关于父亲最深刻的记忆也出现在这里。
虽然懂撂跤,但父亲从不主动出手。用他的话说,不怕事,但也别耍横,做人就这么点规矩。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主动打人就是在二中门口。那时候周河上初三,童年那种源自血脉的天然亲情早已淡漠,相比于跟父亲聊天,他更愿意把心里话写进日记里,然后把日记本甩到某个永远无法记起的角落蒙满灰尘。那天放学,周河正跟同学聊昨天的球赛,一辆轿车闯了红灯,等他发现的时候车轮已经从他脚上碾轧过去,周河当场就趴那了。现场很快被围得水泄不通,司机吓得脸色煞白,闻讯赶来的班主任一着急就嘴瓢,打电话通知周河他爸时说的是“孩子腿断了”。二十多分钟后,父亲挤开人群赶来,司机伸手走过去赔笑,“老哥”两个字刚出口,整个人就被甩开,像面袋子一样在空中划了个半弧,被父亲死死按在地上。一巴掌下去,司机掉了颗牙。父亲眼里满是血丝:“我做人,讲规矩。周河要是腿断了,我也卸你一条腿。”那天周河是由民警陪着去医院的,父亲和司机被带到了派出所做笔录。往后的两个多月,周河只能拄拐行走,偏偏二中往东的那条大坡道正在施工重修,行人只能走台阶。于是父亲每一天都会跟他一起上下学,到了这段路就蹲下身子,周河很默契地趴在他背上,像小时候被父亲背着前行。台阶很长,路边的梧桐树枝繁叶茂,细碎的阳光洒在父亲宽阔的背上,他壮实得像一座铁塔,没人能相信钢铁也会锈烂轰塌。
直到看见有人招手,周河才意识到自己又陷入了回忆。他盯着看了几秒,确定学校传达室里的大爷是在冲自己招手。周河过去给大爷递了根烟,大爷乐了,接过来,夹在耳朵上。
“看你在这儿发愣挺久了,等孩子?哪个班的?”
“没等孩子,找人呢。”
“找谁?”
“我爸。快七十了,国字脸,一米七八,深绿色老头衫配灰色大裤衩。”
“我还真见过,就今天上午,他在校门口站着不动弹,也不说话。我以为他来接孙子,跟他搭了两句话,没想到他说来接儿子。我还以为他跟我逗乐呢。你打他手机不就得了?”
“他老年痴呆,没手机。”
“乖乖,这病可了不得,身边咋能离了人?”
“他最近才严重起来的。走丢过一次,公安局给我打了电话,我从外地赶回来照顾他,到现在才一星期不到。知道他上哪去了吗?”
“早走了。说是跟儿子约好了。”
“约哪儿了?”
“这我上哪知道去。”
摩托车重新发出轰鸣声,但周河不知道该往哪走。不行就只能再去报案找人,但这次可不一定能有上回的好运气。阳光灼热炽烈,远处传来渺远的蝉鸣,周河能察觉到冷汗正顺着脖颈往下流。他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并不完全相同——相比于父亲,他要脆弱得多。
身后突然传来门卫大爷的吆喝:“你爸有啥爱好没?这病就怕挂念,他心里惦记啥,就可能去找啥了。”
这句话来得正是时候。周河如同聆听神谕,再联系起刚才大爷提及的“和儿子约好了”,他心里有了数。他把摩托车油门轰到最大,风驰电掣地上路了。
三十年前,滨县玩冬泳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水平有高有低。论大拿,父亲在里头算一号。一进腊月,老龙头就挤满了冬泳爱好者和看热闹的围观群众,这片形似龙头的沙滩坡平浪缓,适合下水,离岸一公里左右有个石岛。新手大多在岸边扑腾,老手则能一路游到岛上,歇够了再折返。不管挤了多少人,父亲总能从外头悠然漫步到老龙头的最核心位置,认识他的喊声“周哥”给他让路,不认识他的看见这身肌肉,大多也会往旁边让让,想瞧瞧他有多少能耐。父亲的热身方式仍是撂跤那一套,深蹲扎马,扭腰拉筋,捎带再做两个拐子步,等全场的目光差不多都被吸引过来,他就低喝一声,仿佛要把胸膛里的气息全部撕扯迸发,再下水就有如神助。
周河却从不下水。他体格没问题,十三四岁已经壮实得像只小牛犊,但彼时他对父亲的崇敬已经被那些数不清的巴掌扇得消失殆尽,叛逆成为摆在眼前的答案。他极力避免成为父亲那样沉默、粗浅、暴力的人,于是遵循了一个简单有效的逻辑——但凡父亲希望他做的,他全都抵制。于是直到南下打工,周河都从未尝试过冬泳。实际上在他出车祸的那段日子,父子二人的关系有所缓和,父亲曾带着周河来老龙头散心,像是受到某种感召,周河看着石岛上的灯塔,心里涌出一种难言的冲动。
“爸,你游到过石岛吗?”
“数不清了。”
“那你上过那座灯塔吗?”
“嗯。”
“上面啥样?”
“想知道,就自己游过去。”
对话戛然而止。周河很想知道,为何父亲这么冷硬,为何两人的相处永远带着尖刺,话到喉咙里的时候就像烟云般迅速消弭,他悲哀地意识到,父亲也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天晚上,周河离开了家。他怀里揣着自己攒的两百多块钱,心里想,既然两人在一块怎么都拧巴,不如早走,走到哪算哪。公交车在夜幕中穿行,周河的心怦怦直跳,他甚至感觉身后传来了背景音乐,一个宏大的、波澜壮阔的人生即将在他面前展开。路过老龙头时,周河看见有条渡船停在岸边,船头的木牌上用红漆写着“石岛”,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给游客检票。周河几乎是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拄着拐下了公交车,一瘸一拐走过去买了张票。临上船的时候,周河问工作人员:“能上灯塔吗?”工作人员说:“能。”周河捏着票回头看,沙滩上影影绰绰,像父亲站在不远处,仔细一看又消失不见。工作人员问:“还上不上,马上开船了。”周河犹豫片刻,把票塞进裤兜里,说:“不上了。以后我自己游过去。”
快到老龙头的时候,摩托车再也骑不动了。天太热,沙滩和附近公路上挤满了来洗海澡的人,周河只能把摩托车停在附近,一路徒步寻找。刺目的阳光让眼前的一切色彩变得过度饱和,让人不禁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景象要和记忆一样缓慢融化。十几分钟后,周河的脚步突然一滞。远处的沙滩一角坐着个熟悉的身影,深绿色老头衫,灰色大裤衩。人找着了。
周河把鞋脱了,赤着脚走到了父亲旁边。从这个角度看,父亲瘦弱得惊人,他的肩胛骨由于缺少肌肉而异常凸出,整个人佝偻得不像样子。察觉到周河到来,他很慢地转过头,两个眼眸却是完全失焦的,仿佛真正的他正从这具衰老的躯壳里慢慢消失。他的胸前湿了一片,脸颊上有未干的泪痕,嘴角又挂起了涎水。周河弯腰拉住父亲的胳膊,父亲却猛地挣脱开,脸上满是讶异和惊恐。
“你谁啊?”
“我是你儿子。”
“我不认识你。”
“你在这干嘛呢?”
“我等我儿子呢。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我教他冬泳,往石岛游,往灯塔游……他马上就来了。”
“你儿子今天有事儿来不了,我带你回去见他。”
“我不跟你走。我不认识你。”
“回家你就认识我了。跟我走。”
“我不认识你!你再这样我喊人了!”
周围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动,不断有窥探的目光投射过来。烈日刺得周河的脸颊火辣辣地疼痛,他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脑子里,一上午积攒的疲惫在这一秒到达了顶峰。
“跟我回家!”
周河这一嗓子,把父亲吓了一跳。他滚动着喉结咽了口唾沫,抱着膝盖把身子缩得更紧,死死盯着周河的手掌。几秒钟后,周河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老头是怕自己扇他巴掌。周河的心脏像被一杆长矛狠狠洞穿,他恍然间意识到,时间在他和父亲之间完成了一种调换,悄无声息,又剧烈至极。
周河盘着腿坐在了父亲身边。他伸出手,很慢很慢地把老头嘴角的涎水擦干。
“爸,我把你弄丢了。”
父亲平静下来。他没有任何回应,不知又陷入了哪段破碎的记忆里,失焦的目光再次转向远方。不知怎的,原本干燥灼热的天气里突然刮起了风,周河被迷了眼,捂着脸揉了半天,之后浑身颤抖,最终变成嚎啕。
他没看见,无数细沙被风托起,在他的身旁打了个旋儿。
【作者简介】胡玉晗,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青年作家》《上海文学》《山花》等刊,参与《大唐飞歌》《梦中人》《黑鸟》等多部影视作品、舞台剧的编剧工作。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