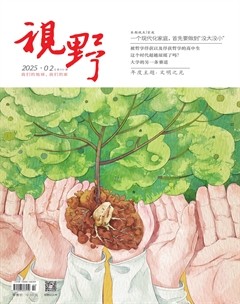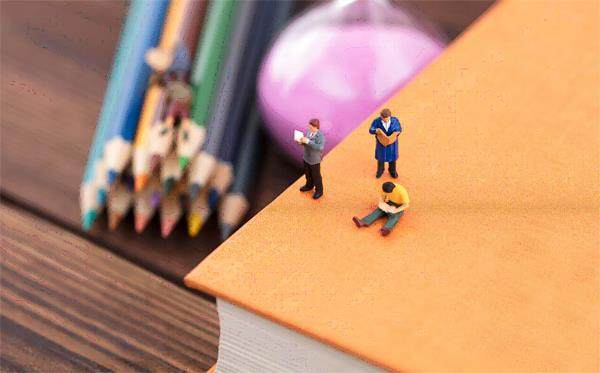
壮志雄心
我是2010年由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保送的北京大学,专业是电子信息与技术。博士阶段,我的研究方向和人工智能打交道比较多。2019年博士毕业时的就业选择蛮多的,比如高校教职、投资银行、互联网大厂之类的。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这并不是一个“躺平”的决定。“成为中学数学老师”,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已经盘桓了六七年。读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认定:想要改变一代人最快的方式,是出现在他们形成世界观最关键的中学时光里。大学时期,我对自己的成长环境有过反思。我感到,我们这代——至少我看到的北大的学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我们这代学生的目标性非常弱。我刚上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所有人想的都是考GRE,刷GPA,然后去美国读一个很好的学校,但是具体为什么要这样,很少人说得清楚。带着一点理想主义,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假设清华北大两所高校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追求只是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不是有点可惜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做一些有可能引领时代变革的事儿呢?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也曾经努力把绩点刷到了专业前列。可心中那种隐隐的“不对劲感”变得明确起来。我意识到,即便北大学生也在延续面对中高考的学习态度,而大学专业课的考试方式和中学考试依旧相通。应试类考试检测出的是一个人有没有用心学,但考95分的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未必比考80分的学生高,没准只是他猜老师出题方向的水平更高。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陆续参加了一些校级学生社团,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们的交流多起来,观察的视角从自己转到了他人身上。我发现即使在北大这个优秀生集中的群体,学生的思维模式也容易固化在学科内部。比如物理专业的同学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可能会以自己不会编程或者编程能力弱为由,卡住不做了。我很困惑:当我们面对一个现实或科研的问题时,难道不是应该能往前迈多大的步子,就先迈多大步子试一试么?对于专业以外不熟悉的内容,以北大学生的能力,不应该很快就能自学会么?我猜想,我们这代人缺失以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与之相伴的快速学习能力,以及对于不同学科思维的包容态度等等。这些东西的缺失,或许根源在中学。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青少年接受的只是应对标准化考试的教育,就很容易认可在每个学科内,每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答案。如果中学生不断被提醒“在数学考试中不要用物理学的论述方法”、“信息课高考不考不重要”、 “纸笔考试不接受近似解”、“高考不让用计算器,所以算对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见到问题先掏纸笔开始推演”,“学科之间应该有严格界限”。到了大学,这些固化的思维定势可能已经改不动了。在大二、大三形成了职业规划的雏形后,本科毕业我选择了直博。我想把专业学习这条路走到头,我的个人科研经历也会对未来的学生们有所启发和参考。博士毕业后,我顺利通过校招进入北京一所知名中学。
工作前,我已结婚、买房,经济上压力不大。我太太很鼓励我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父母对我一切人生重大选择均不干涉。作为北京的中学老师,在不愁住房的基础上,衣食无忧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有了物质基础,我梦想着可以对中学教育做出点刷分以外的改变。
数学到底教什么
入职中学后的头两年,我在工作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我在初中部教三个班的数学课。一般来说,新老师容易把控不好课堂纪律,但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是通过竞赛保送北大的,也曾经在北大专业绩点排名前列,学生们对我有一种“天然崇拜”,具体表现就是听讲比较认真。对教师这个职业,我适应得也很快。博士生教中学不存在技术难题。只要认真,教学技法上的打磨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差不多都能掌握到位。而且因为教的是初中,我不直面高考,压力也没有那么大。那时候,我上课比较“放飞自我”,比如讲着讲着就不按课本来了,开始在某个点上进行深入探究。因为学生的素质普遍很高,我按照什么方式讲,其实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太大,学生们也都挺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