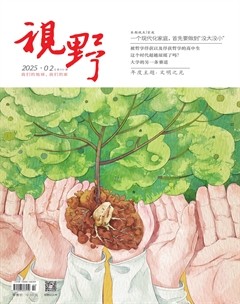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学者的中文名字都十分具有迷惑性:
费正清、孔飞力、施坚雅,乍一听是不是都以为是中国人?
其实,给自己起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可能是这些人的“标配”。所以,有学问的外国人,是怎么给自己起中国名的呢?
远道而来,入乡随音也随俗
公元717年,这位一心入唐求学的日本贵族——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一说阿倍仲麿)费尽艰辛远渡重洋,终于如愿踏入长安。在长安太学读书期间,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汉名——仲满。在加藤隆三木为其所著的传记小说中,仲满的第二次得名——晁衡,不仅是玄宗李隆基钦赐,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朝’里有‘日’,‘朝’‘晁’相通,嗯,‘晁’字不错。姓里给你放一个‘日本’的‘日’字。西汉有个晁错,知道吗?就是这个晁错的‘晁’。名字嘛,‘衡’字如何?均衡的衡,你性格平衡而中道。衡里有鱼,连年有余,不愁吃穿。”
虽然情节多少存在文学加工,却也把“晁衡”二字的内涵解释得明明白白。晁衡没有辜负这个名字(日本毕竟也是东方),余生几十载都在自己仰慕的唐朝出仕为官,深得玄宗信任,更与王维、李白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多年后,晁衡东归,途遇暴风雨,长安的故友以为他已经遇难,悲痛不已,李白还满怀凄伤地写下一首《哭晁衡卿》,用一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诉尽了对这位日本友人的思念和痛悼。
比起晁衡的诗意浪漫,后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取名时便多了点别的考虑。
16世纪开始,第一批耶稣会士在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下陆续进入中国。千里而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在东方世界传播西方教义。然而,要想顺利传教,头一个阻拦在传教士们身前的便是文化这关。
以最快速度融入中国社会,成了传教士们最紧迫的任务。
改名,成了一个好办法。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琢磨过这个法子。这位出身意大利贵族的耶稣会士,全名玛泰奥·利奇,中文姓名“利玛窦”,分别来自他本姓第一个音节Ri的音译,以及名Matteo的音节。据研究者推断,“利玛窦”这个名字,和中国文化或诗情画意的关系其实不大,反倒是利奇为了“文化适应”选了一条捷径——“入乡随音”,将本名改写改写,得了一个让大家好懂好记的中文名,这下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不就简单方便多了?
不止利玛窦,同时期许多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把“入乡随音”玩得挺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