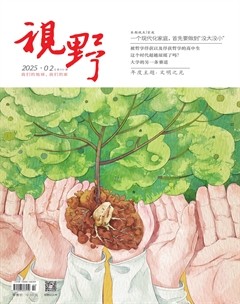约翰·契弗,美国小说家,他流传最广的一篇小说,大概就是《巨型收音机》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吉姆和艾琳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住在一栋公寓楼里,有一双儿女,雇着一个女仆,两个人每个月都会去剧院看戏,闲暇时间喜欢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听古典音乐,这是夫妇两人和邻居及朋友的一大区别。为什么呢?有一位法国学者叫布尔迪厄,他说过一段话:“对于一切低俗、露骨、粗野、贪婪、奴性的享受方式之否定,是神圣的文化领域之构成要件,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懂得享受庄严、优雅、无私、高贵的人之肯定——其价值是那些俗人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文化消费总是有意识而且刻意或非刻意地在执行一种功能——把社会差异正当化。”
法国知识分子说话总是比较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听古典音乐的人,比看综艺节目的人高级。艺术消费就是区分高级和低级。布迪厄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资本”,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或精神需求,你的社交,你的尊严感,你的自我实现,都是基于文化基础的需求,都需要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比收入更能体现阶层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文化资本就是用来造成阶层差异的。吉姆和艾琳爱听古典音乐,是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资本:虽然都住在一栋公寓楼里,但他们不是一般的俗人,他们是有可能搬到高尚住宅区的。
可惜,家里的这台收音机有点儿小毛病。有一天吉姆正在听舒伯特,收音机不响了,怎么拍打都没用,吉姆就答应媳妇,马上买一台新的。第二天,收音机就送到了,个头儿很大,上面有很多按钮。艾琳觉得,老公挑的这个收音机太没品位了,和家里的风格一点儿也不搭,这个大块头显得太突兀了。艾琳有一件鼬皮大衣,染得很像是貂皮大衣。她对自己的起居室很自豪,像挑选自己的衣服那样选择家具装饰,进行颜色搭配,结果丈夫买来的收音机是丑陋的胶木盒子,有很多调谐按钮,打开还发出一道绿光——实在是太难看了。
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凡勃伦,他写过一本书,《有闲阶级论》。他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个词,那些又贵又能炫耀的东西被称为“凡勃伦商品”,只要一说到消费主义就会提到凡勃伦。这台收音机算是凡勃伦商品吗?凡勃伦说过,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维护体面的斗争,要赢得自尊,就要时不时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支付能力。可是,光有支付能力还不够,这台收音机四百美元,是个奢侈品,但它在审美上没能达到艾琳的要求——花了钱却没买来体面。
更要命的是,这台收音机的杂音太多了,听着莫扎特,就能听到里面传来电话铃声、电梯运转的声音、吸尘器的声音,来自左邻右舍。厂家来修理过一次,没修好。吉姆和艾琳待在家里,就能通过收音机听到邻居家的生活:谁家的保姆正在给孩子念童话,谁家的女人找不到袜子了,谁家正在办派对。两人偷听邻居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好笑,可夜里,公寓楼的灯光都黑下来之后,艾琳听到一对中年夫妻克制又伤感的对话。丈夫问妻子,身体如何,要不要换个医生看看。妻子说,现在这个医生的账单已经很吓人了。艾琳听了这话,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平静的生活不能细琢磨,细琢磨起来,养老的问题、资产配置、疾病和保险,这些事儿都让人发愁。
可艾琳还是忍不住会通过这台收音机偷听邻居家的生活,其中有虚荣,有信仰,有绝望,有罪恶——她很痛苦,也怕邻居能通过别的什么电子产品听到她家的动静。丈夫吉姆就告诉她,她既然很痛苦,就不要再偷听别人家的生活了吧。妻子艾琳说:“生活太糟糕,太肮脏,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