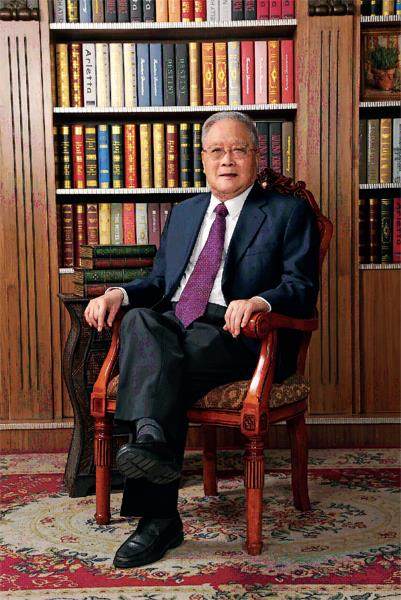
陈光中95岁了。眼下他最苦恼的事,是失眠。
年轻时就有的轻度睡眠障碍越来越严重,他常常凌晨才能入睡,有时甚至整晚睡不着。辗转反侧,难免东想西想。
最近他夜里考虑最多的,是准备开设的生平展览馆,对定名为“陈光中法学书馆”还是“陈光中法治书馆”徘徊不定,目前初步定名为前者。馆址在老家浙江温州的永嘉书院,已经开始施工。
除了个人私事,像已经提上议程的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政法大学疏解到雄安等大事,也都会在夜里涌入他的思绪。
让他回味起来感到愉快的是去年出版的《陈光中口述自传》被评为优秀传记作品。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像江平起伏那么大,故事那么多,没想到平平淡淡的传记还能获奖,可能是因为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很有代表性和记录性吧。
《陈光中口述自传》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说,不少读者告诉他,他们曾因陈光中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的“平庸”和20世纪50年代在老校长钱端升受批判时发过言而对他颇有偏见,这本书让他们更理解了陈光中,也看到了他晚年的变化。
但其实陈光中心中的天平似乎并没有过太大的倾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但“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像他毕生研究的刑诉法一样,讲究的是平衡之道。
“做学问我是有信心的”
1990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孙国栋这一届毕业时,江平已被免去校长及校党委委员职务,陈光中以常务副校长身份主持学校工作。因此这一届学生的毕业证上,校长签名是“陈光中(常务副校长)”。
孙国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他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更希望毕业证上的校长签名是江平。毕业典礼结束后,他直奔江平家,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题词。那时陈光中作为校长的光芒似乎被江平遮蔽了,相较于江平的雷厉风行,他显得有点温温暾暾。
此后校长职位空缺了近两年。直到1992年5月16日,司法部才正式任命陈光中任校长。
那时校内经常有对话会。因住房和食堂等种种问题,青年教师要求跟校长对话,毕业留校的孙国栋就是代表之一。在会上,孙国栋发言犀利,毫不留情。他回忆,陈光中被呛得有点下不来台,他微微低头,目光越过眼镜上方盯着孙国栋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这之后,孙国栋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读过《陈光中口述自传》后,孙国栋理解了陈光中当时的处境和性格。
陈光中的父亲曾是永嘉县参议会议员,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后自尽(改革开放后平反),叔父担任过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1949年后去了台湾。陈光中为此背了多年的政治包袱。他在反右运动后期被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开除团籍,离开了刑诉法教研20年。他早早就意识到,他的前途只能是在学界。
孙国栋了解到,陈光中其实有外圆内方的一面,在主政中国政法大学期间顶住了很多压力。那时经费紧张,又在建设昌平新校区,陈光中勉力支撑,难免无暇顾及教学改革。
1994年4月,陈光中不再担任校长之职,这离他上任还不到两年。上午宣布免职,下午他就搬出办公室,毫不留恋。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那时正在陈光中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记得,陈光中卸任校长后完全没有失落期,反而因为能专心做学术而焕发了更多神采。
陈光中自己曾说:“做学问,我是有信心的。”1984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成立,他连续四届被推选为会长,执掌诉讼法学会22年。1986年中国政法大学获批成立全国唯一一个诉讼法学博士点,整整九年间,他是全国唯一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
1995年12月,陈光中弟子、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的卞建林协助陈光中成立了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作为开展中外刑事法学合作和交流的基地。
卞建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光中做校长时没能充分施展的行政能力在中心主任位置上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他组织对外学术交流,举办研讨会,做得有声有色。在海峡两岸及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他那种谦谦君子、游刃有余的开阔学者气质显得尤为突出。
推动刑诉法的突破性改革
卸任校长后,陈光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是参与刑诉法修订。
新中国首部《刑事诉讼法》1979年颁布,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部刑诉法的立法十分仓促,不免失之粗疏。进入90年代,刑诉法修订被提上立法议程。
刑诉法又称“小宪法”,完善其基本制度的敏感度要远大于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