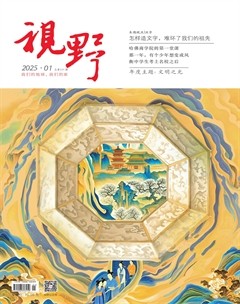一
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因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
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
另据胡乔木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
关于“汉字简化”与“文字拼音化”之间的关系,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说得非常清晰:“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
这种“过渡性质”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成员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
二
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共收入简体字700个。该稿送审后,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文改会依据“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指示精神进行修改,但在具体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这个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
第二稿送审后被驳回,理由是简化字数量太少——第一稿送审反馈回来的指示是“700个不够”,第二稿只剩338个,被驳回也是情理中事。随后,文改会又通过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等手段,拟出了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
“國”字的简化在50年代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但很多文改会委员不同意,认为封建色彩太重,后遂加一点改为“玉”。
第三稿引起了社会各行业的普遍反对。对印刷部门而言,第三稿意味着他们需要重铸1600多个铜字模,简直是灭顶之灾;草书写法的收入,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以前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系统,全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于是,第四稿又将印刷体简化字缩减为600个。
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对外公开。今天回头审视,这个《草案》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试举几例:
(1)文改会曾定下不造新字的原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比如,“瞭解”的“瞭”,明明有约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却非要臆造一个之前从未存在过的新字“( ))”。
(2)一味追求减少笔画,往往放弃常用本体字,改取异体字。比如,“足迹”的“迹”,本该选用本体字“跡”,仅因“迹”字笔画略少,就弃“跡”不用。
(3)1500个常用字(以教育部当年所公布者为准),《草案》只简化了335个,这335个简化字,只占到《草案》简体字总数的22%。也就是说,《草案》中78%的简体字,并非常用字。由此可见其工作重心,已严重偏离了方便民众日常使用的初衷。
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出台。《方案》确定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该《方案》有两个问题:
(1)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但未达到“普遍约定俗成”程度的简体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当时均尚局限于部分行业使用。
(2)收录了不少新造之字,如仓、齿、块、伞等,均是以前并不存在的新字。
这两类简体字,占到了《方案》简体字总量的31%。它们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两大不便:
(1)新造简体字面貌陌生,语文教学遭遇了巨大困难。如“倉”被简化成了“仓”,但方案并没有将“搶”简化成“抢”,于是,学生不但需要学一个全新的简体字“仓”,旧有的繁体字“倉”也不能丢,既增加了学习负担,也显出“倉”字的简化毫无意义。
(2)《方案》带动了民间自由造字的风潮。有学者评价称:“由于《方案》在简化偏旁的使用范围方面,交代得不够明确,以致各简各的,使汉字的混乱达八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