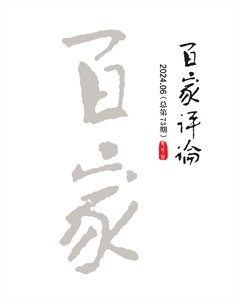内容提要:当下对于陈河小说的阐释经常是以空间为主导,遮蔽了陈河小说时间维度的特征。自2005年作家重返文坛以来,回溯和回忆构成陈河小说的基本时间视角,小说具有通过回到过去来再现空间的形式特征。因此,本文将陈河2005年回溯视角的小说分为个体记忆、考掘历史、在地书写三个主题加以讨论,考察小说是如何通过书写过去形构原乡和想象的空间,以及,如何将新移民主体当下的生存体验、离散经验安顿在过去时空之中。
关键词:陈河 回溯 离散 想象原乡
一、过去是故乡也是异地
陈河在《沙捞越战事》和《女孩和三文鱼》两部作品中都不惜大段篇幅,介绍三文鱼“奇迹般的生命循环”a:在淡水孵化,游向海洋成长,洄游至淡水产子,最后死亡。有趣的是,陈河从2005年重返文坛以来,似乎也遵循着某种创作的“洄游”规律,只不过是在时间之流中洄游: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都是建立在史实之上,文本内外都能看到大量的史料考证,因此可以归入历史小说的范畴。尽管《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写的是中国之外的华人历史,《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中也不乏对于外国人的历史书写,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仍倾向于将陈河的文学创作纳入“中国故事”的序列,如刘艳曾说:“近五年以来乃至新世纪以来,在严歌苓、张翎、陈河等海外华文文学代表性作家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中国叙事’或者说‘中国故事’的讲述,旧有的‘离散写作’、‘离散美学’等术语,已经无法概括和囊括愈来愈呈现新变的他们的创作”b,张娟更是把《甲骨时光》作为海外华人写中国故事的典范c。“中国故事”显然是空间为主导的阐释话语,用此框架检视陈河的历史小说难免遮蔽了小说时间维度引发的问题:陈河为何钟情以虚构的形式书写过去的时空?如此再现的时空具有怎样的特征?作者以历史为材料以虚构为形式的创作策略又暗示出怎样的离散、反离散或不自觉的新移民主体?本文试图从陈河2005年以来小说创作频繁出现的回溯视角探索作者究竟写出了怎样的过去的故事,以及其中暗示了怎样的新移民主体。
陈河的回溯视角并不是只出现在历史小说中,早在回归文坛的第一部作品《被绑架者说》就显露出来,小说如此开始:“我离开阿尔巴尼亚六年了”d,此刻在多伦多家中看电视,却因为一则电视新闻,“那些已经模糊暗淡的人脸现在又渐渐浮现,令人战栗地微笑起来。”e其后无论是阿尔巴尼亚系列、北美系列、南方家乡系列的小说,不乏以回忆过去展开的叙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河身处异国书写在地经验时也时常选择一个回忆的视角,例如《水边的舞鞋》中,主人公的舞鞋之虑并非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出现,而是始于回忆:“现在想起来,丁加舜如果没有看见游泳池边杉木平台上那几双芭蕾舞鞋的话,他不一定会买下这座房子的。”f此前,学界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陈河小说中的空间所指,不管是温州还是吉诺卡斯特,指认的都是一个凝固、本质的地名,而忽视了小说叙事往往具有通过回到过去来再现空间的形式特征,回到过去意味着需在记忆与遗忘、历史与想象中抉择和权衡,在这个过程中,空间成为流动、可变的地方,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过去构形了怎样的空间?
首先,在回溯时间的过程中,空间被构形为实际(virtual)的或隐喻的原乡。以书写过去、记忆、历史抵达某一空间似乎成为离散作家的共识,如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又或是张翎的《余震》,离散作家对于过去的情结完全不亚于对于原乡的情结,拉什迪《想象的家乡》一文在“过去”与“家乡”之间作出极为精辟的论断:“过去才是家乡,尽管那是一个早已失落于时空中的家乡。”g拉什迪以空间隐喻时间,构建了时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极其抽象的方式揭示了一种人类普遍的处境:“如果说过去是一个国家,那我们都注定要从这个国家出走,失却这个原乡是全人类普遍的命运。”h显然,离散族群是这一普遍命运的提喻,更是最为极端的范例,他们不仅失却了时间的原乡,也失却了空间的原乡。矛盾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乡失去,我们必须要重返原乡以获得当下的身份认同,因而原乡既是失去的又是需要追回的,追回是一种记起(remembering),唯此才能“再次把自己投入熟悉的框架,也正是通过这个框架离散族群确证他们的历史、谱系、身份,以及最为重要的——归属感。”i记起过去并非是单纯记起一个时间节点,而是记起一个时空情境,它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来源。
将过去的空间构形为原乡并不是要赋予它本质意义,相反,过去的空间同时也是可以被重构的。斯图亚特·霍尔在谈及有机社群(organic community)、集体性(collectivity)时说到,当我们回忆过去时,“我们总是将过去重塑得更为本质、同质、统一”j,“重塑”一词清晰地揭示回忆不仅仅是再次回到,也有重新塑造的可能。我们依靠两种形式记忆过去,一种是照片、博物馆展品、纪念碑等物质形式k,另一类是语言记录,前者是过去的物质基础,后者是过去的叙事基础。在历史小说中,即一般所说的“将真实或虚构(或二者皆有)之人、事,与某一引人深思注目之历史时空交织形成的作品”l,两种形式更是密切融合,这提醒着我们小说再现过去不仅是发掘、转述史料的过程,也是虚构、转义m的过程,书写者不仅从过去获取经验,同时也将当下的经验融入对于过去的书写中。这一点对于理解离散作家的历史书写尤其重要,我们不能只关注其历史的一面,也要关注其小说的一面,小说即意味着想象,而想象意味着将“范围更广阔的人生经验”n纳入叙事,想象成为离散作家将当前的生存经验纳入历史、原乡必须借助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拉什迪提出离散作家所写的过去是“不可见的、想象的、脑海中的家乡”o。因此,我们说记忆中的那个空间同时也被形构为承载着历史与虚构、记忆与遗忘、原乡情结与在地经验,多种矛盾因素分离、碰撞、融合的实验场所、想象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不仅是我们要不断追回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动身前往的异地他乡。
本文将陈河2005年回溯视角的小说分为个体记忆、考掘历史、在地书写三个主题加以讨论,考察小说是如何通过书写过去形构原乡和想象的空间,将当下的生存体验、离散经验安顿在过去时空之中,以此揭示出为“中国故事”所不见的北美新移民写作状况。
二、个体记忆的召唤:扩写、重写《布偶》
陈河在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布偶》的创作基础是他1988年在浙江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p。尽管长篇保留了短篇绝大部分的情节、人物,甚至是原文,最终却展现出与短篇截然不同的文本气质,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短篇具有较强的现代主义特征而长篇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结合作家1994以来的侨居、移民经历,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对于作家1974年至1975年在温州一家华侨纺织工厂的真实经历的回溯与虚构,短篇和长篇文本具有怎样的异同?由此可以看出怎样的作家主体转变?
短篇和长篇均以几乎一样的句子开篇:“如今我常常被一些旧的记忆吸引到我以前做过事的地方去,沉浸在一串串白日梦里”q,不同仅在于短篇是第一人称“我”,长篇是第三人称“莫丘”。如前文提到,以回忆过去展开故事的回溯视角是陈河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布偶》也不例外。从作家的真实经验角度来看,尽管短篇和长篇都是写同一个时空中的故事,回忆的跨度以及范围却有显著不同:短篇是作家在1988年写1974至1975年的故事,跨度在十五年之内,而长篇写于2010年,距离这段时间已有三十多年;更为重要的是,跨度之差又带来了回忆范围的差别,短篇小说只涉及1988年之前的作家经验和记忆,而长篇小说显然能够触碰更大范围的个体历史;范围之差提示我们长篇可以追溯作家1988年写作短篇的经验,反之的预测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长篇本身已经是对于短篇的回忆,短篇成为长篇回忆的源泉之一。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长篇的叙事进展高度依赖短篇的结构以及具体的内容,有时甚至是对短篇的逐句扩写,如两个文本都是以介绍故事发生的时空开篇,短篇除了点明时间“文革中期”,空间描述上刻意模糊了故事发生地点的坐标,仅说到“城西街区那一座青灰色的用花岗石砌成的哥特式教堂”,而长篇在保留这个描述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指出年份1973年以及地点南方老家W州,甚至连短篇中柯依丽手指间的“一枚铅坠子”r,长篇也为其补充一个柯依丽与葡萄牙文成华侨的婚约背景。除了对于短篇中局部细节信息的增补,长篇更为重要的叙事动力在于对于短篇中人物的扩写,也就是将他们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短篇中主人公“我”热衷于窥视的当地侨领裴达峰“他的年龄、经历、家族、个人爱好情况人们也一概不知”s,长篇则花费三章交代裴达峰的出身、教育、恋爱、从医经历,有趣的是在叙述裴达峰的经历时,作者再次召唤记忆的缪斯“记忆像是一条隧道,似乎能通到最初的源头”t,无疑又是一次回溯,又如长篇中还将主人公莫丘和柯依丽的爱情悲剧作为主线故事来写,而短篇中的“我”对于柯依丽的爱慕则止于花园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