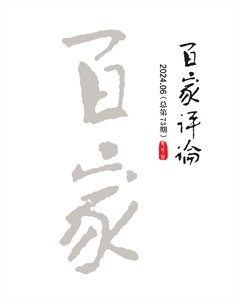内容提要:方远的《大船队》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它完成了人与海洋关系的探索,在大海的流动中,呈现出人类命运的无常律动。它更以一种深厚的文化视角观照了胶东大地的各个维度,包括生动的事物细节、文化细节和生活细节,展现出立体的画面感和独特的气韵。同时,《大船队》通过个人命运折射出民族的历史变迁,为时代巨变做出了解释和描摹。
关键词:方远 《大船队》 文化意蕴 家国情怀
方远的长篇小说新作《大船队》以史诗的笔法,书写了胶东大地激荡巨变的时代风云,同时又通过一种细腻的目光来刻画生活细节,显示出穿透现实的力量。其中既有人与海洋的关系、山东文化的独特韵味,还有面向时代的家国情怀。《大船队》沉浸于波谲云诡的氛围中,在变幻莫测的历史迷雾中,向大海迈进。
一、人与海洋关系的深刻体悟
近年来,方远将自己的笔触转向了海洋,《大河入海流》和《大船队》等都是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显然,作家选择海洋作为书写对象并非偶然,《大船队》从莱州湾出发,走向辽东湾,覆盖了大半渤海海域,具有广阔的叙述空间。方远曾在访谈录中提到:“从陆地走向海洋,更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仅从小说本身来说,海洋具有某种积极的、现代的象征意义。”a可以看出,《大船队》既有人文情怀,也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与传统的海洋书写的固定视点不同,《大船队》生成了海洋与土地的动态离合,莱州湾人民传统的陆地生活与驾船奔向海洋构成小说最具张力的时刻。尽管方家村距离大海只有五里多,但周围均是肥沃的良田。方继先作为宏德堂的上一代,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他通过有效的经营和节俭的生活方式,逐步将宏德堂的土地从最初的五十多亩扩展至如今的百余亩。然而,宏德堂现任当家人方英典具有雄心壮志,他突破了传统土地经营的局限,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海洋领域。方家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农业种植为主,仅有少数几家富裕的大户人家拥有渔船,从事渔业生产。但在方英典的战略构想中,土地已无法满足他对宏德堂的未来构想,海洋才是他施展才华的真正舞台。他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毅然决定组建货运船队,为此特地从蓬莱聘请了专业的造船团队,开启了宏德堂的海上之行。这蕴含着掖县人对海上货运的想象,即不同地理空间通过海域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宏德堂在海洋与土地两处地域空间中转换,反映出历史与当下,“种地的敬土地老爷,出海的敬海神娘娘,各有所敬,既井水不犯河水,又异曲同工,一脉相承。宏德堂人以种地发家致富,逢年过节自然敬的是土地爷。但是,今天,八月十八日,宏德堂将要离开祖祖辈辈辛勤耕耘的黄土地,驾船奔向好汉的海洋,就得敬海神了。”b小说呈现了宏德堂不同代际继承人在经营模式上的变更,从方继先以土地为生到方应典建立大船队开拓海上货运,海洋主动参与到小说故事的演进中,成为场域性的存在。
在《大船队》中,人与海洋是对立统一的,海洋如镜像,凸显出存在与死亡的交错熔铸。一方面,大海为人们提供了谋生的新途径,他们通过海上货运维持生计,享受着海洋带来的广阔与自由。大海蔚蓝,天空也蔚蓝,海天一色,无比壮观。货船被波浪翻滚的大海紧紧地包围了,海鸥欢快地叫着在浪花里捕食。这一类景不仅展现了海上货运的壮丽景象,也反映了人类与海洋之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海上货运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许多人因海上事故而丧生,他们的生命在浩瀚的大海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船翻人亡的事时有发生,许多不幸的人就客死他乡了,有的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有时候,人过了几天才被潮水推到岸上,已是面目全非,甚至连家人也认不出是哪个了。”c大海作为一个充满变数的自然力量,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时而疯狂地玩耍,时而安静地沉睡。这种变化无常的特性使得大海既具有迷人的魅力,又充满了未知与危险。作者对大海的描绘不仅丰富了《大船队》的文学色彩,也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与探索精神。《大船队》通过生动的笔触书写了海上货运对人类社会的双重影响,既展现了人类与海洋之间的相互依存,又揭示了海洋的残酷与无情以及人类在它面前所表现出的脆弱与无奈。小说中人们向海而生,也要承担海洋带来的危险。人与海洋之间并非浪漫的、精致的,而是现实的、残酷的。
同时,在《大船队》中人与大海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互相敬重。这里的“大海”不仅作为海上货运的渠道,也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化身为某种神秘的力量,仿佛主宰着人类的集体命运。方英典经历过一次海上风暴后,认为是海上的“岛礁”让宏德堂人与货船化险为夷,“它们是救命恩人。他决定,从岛礁上请回一块石头,运回宏德堂,安放在牡丹园前,从此保佑宏德堂的货船。”d每次货船出海,管家潘士光都会准备好供香和纸钱,“陪方英典来到礁石前,焚香烧纸,嘴里念念有词,感谢礁石的救命之恩,祈求礁石保佑货船平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