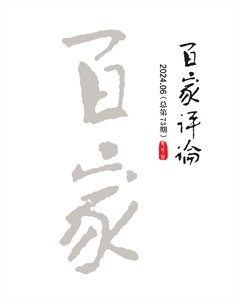内容提要:迟云将写作视为神圣的事业,沉潜于宇宙万物,起兴于个人感悟,以其充满理性和哲思的灵性书写在当代诗坛独树一帜。诗人在诗歌中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痛苦,诗歌中的自我挣扎在集体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白天与黑夜之间。在经历了精神的痛苦挣扎之后,诗人获得思想的澄澈和启悟,他在乡村记忆、灵性自然、诗歌书写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在审视内心世界的同时与前辈诗人对话,通过个人独特的审美体验透视时代的变化,传递出哲理的光芒。
关键词:迟云 矛盾 乡村 城市 自然
迟云的诗歌是非常真诚而且纯粹通透、充满灵性的作品,在诗歌中传达了对于人生、社会、人性的深切思考,既有睿智的眼光,又有人性的关怀悲悯,有对于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犀利认识,同时也有毫不留情的对于自我的审视与反省。诗歌中体现了作者在理想与现实背离下形成的自我分裂,诗人大胆地袒露内心的挣扎、精神的困境,敢于直面灵魂分裂的矛盾与挣扎。诗人将眼光投向了静谧广阔的自然,在孤独的行走中聆听世界万物的本真言说,在诗歌的书写中挥洒率真自由的性灵,在与经典作品的对话中安慰了孤独的灵魂,从而消解了现实与梦想撕裂的痛苦,获得了生命的和谐圆满。
一、欲海沉浮的矛盾之我
迟云是一位典型的“60后”诗人,上大学期间正值文坛上风起云涌的80年代,“本质上仍属于一个具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烙印的理想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精神求索的道路上踽踽独行,苦苦跋涉”。a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诗人的心中始终怀揣着理想的火焰,在欲望泛滥的都市社会中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的矛盾,“现实与梦想,寻找与失落,逃避与陷入,构成矛盾的复合体,道出了一个职场诗人复杂的心声,真实,纠结,有深度”。b
散文家周作人曾幽默地宣称,自己的心中住着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其作品中流露出高雅淡泊的士大夫风范与叛逆野性的流氓气质,创作了平和冲淡与浮躁凌厉两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而在迟云的作品中,呈现了现实之我与理想之我的分裂,现实中的我西装革履,在职场中挤压着自己的灵魂,默默无闻地成为了城市机器中一颗螺丝钉,“我就是契诃夫笔下的公务员/灵魂被附体/思想被打结/纵是心中想着一百个情人/纵是想穿过整个世界去睡你/却迈不开腿上的脚”(《在现实与浪漫的夹缝里》)。理想中的我神游物外,在文学的天地中自由翱翔,灵魂在回乡的小路上游荡,保持着独立清醒的自我反思,“灵魂独上高原/因为自由无羁/因为超凡脱俗/如一棵不和谐的树独饮苍茫中的美丽和孤寂”(《独饮苍茫中的美丽和孤寂》)。
诗人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的心境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著名的意象“死火”。诗人在青春年少时豪情万丈,睥睨世间,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过社会的历练之后,胸中那团燃烧的青春之火已经冻结,“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c死火面临着冻灭还是烧完的两难选择,最后选择不如烧完。燃烧意味着生命无可挽回的结束,而冻灭则昭示着人生难以摆脱的逆境,而诗人也承受着灵魂撕裂的痛苦,“经常陷于此岸与彼岸的困境”(《穿越》)。渴望寻找精神的家园,但无法做出毅然决然的选择,“假如我是一支香烟/很难断定自己是否渴望燃烧”(《很难断定自己是否渴望燃烧》)。如珊瑚般绚烂多姿的“死火”已经蜕化为随处可见的“香烟”,是否燃烧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不过是一支燃烧了一半的烟卷,在诗人的眼中也许代表着往昔生活的回忆,在他人的眼光中这只是不值一提的生活碎片而已。
(一)诗歌中的自我挣扎在集体与个人之间
屈原在《渔父》中提到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究竟做一个目标坚定、清高孤傲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做一个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现实主义者,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纷繁的现代社会中,诗人感觉自己是一粒沙子,是一粒平凡而又沧桑的沙子,习惯了被动地接受外在的苦难,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沉默,“沙子是不会有情绪表达的/沙子已经习惯了被有意无意地强暴”(《沙子在任何时候都是沉默的》)。一粒普通的沙子,对于自己非同寻常的经历闭口不提,过去的繁华人生不过是幻梦一场。“经历过岩浆的迸裂喷发/经历过斗转星移的分裂风化/却始终不说一句话”。岁月的沧桑早已经磨去了个人的棱角,“在孤独中磨平一切无意义的幻想”(《潜入沙子的内心》)。
个体无法抗拒这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有时候难免进行妥协。诗人在灵魂撕裂的痛苦中行走在人生道路上,他悲天悯人,对步履匆匆的现代人充满了隐忧,“谁都改变不了总体的运动方向/谁都逃脱不了内心冲压膨胀的熬煎/真担心若干年以后,呆头呆脑/你我都变成只有躯体没有思想的啤酒瓶子”(《都市心境》)。迟云用千篇一律、形状粗短的啤酒瓶子来形容大腹便便的现代吃货,可谓形神兼备。
(二)诗歌中的自我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在迟云的笔下,都市的生活节奏加快,都市人容易被欲望蒙蔽双眼。这与沈从文批判都市文明、赞美自然人性的文化立场是一致的。沈从文发现都市中人来人往,“可是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d
在诗人的眼中,尽管都市中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充斥着欲望的诱惑与陷阱。诗人借用动物行走的姿态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索。“像狼狐一样游弋/像鹅鸭一样蹒跚/或磊落或猥琐,每个人的行走/都能在动物界找到仿生的影子/也有一些人腿脚健全/却丧失了行走的思维和功能/他们习惯了匍匐爬行/如冰凉的草蛇/在人丛里涎着笑脸,不停地/滑动”(《关于行走》)。物质的诱惑不断激发人类的欲望,“欲望/让一些人灵魂出窍/如隐形的苍蝇/听不见嗡嗡的声音/但传播着腐烂的病因”(《膨胀的鬼魂渴望去飞》)。
诗人无奈地发现,“身子在城里/灵魂在故乡”。乡村是人们灵魂的栖息地,是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但是,那个美好的田园乌托邦似乎遥不可及,诗人的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不断在衰败,父母已经老去,诗意的乡村世界只能留存在记忆中。“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风烛残年/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歌声/催生出一行忧伤的泪滴”(《故乡的秋叶》)。诗人只能无奈发出一声叹息,在水泥钢铁构筑的都市丛林中怀念着记忆中宁静和谐的故土,“这是诗人对于精神建构的呐喊与叹息,迟云的叹息也与沈从文、老舍、曹禺一样,充满了现代化进程中对过往传统和文化的留恋与无奈,而呐喊则至少能证明诗人如殉道者一样的执着向往,一样的努力超越”。e
(三)诗歌中的自我徘徊在白天与黑夜之间
“‘世界’是阳光在大地之上的一件得意之作,它使大地上的一切都敞开了,成为一个日常喧闹的世界。而夜的宁静、朦胧和神秘则解放了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让人发现白天所没有的另一种真实。于太阳的炽热和强光之外,另辟一个清凉幽邃的世界,一种月光下的诗意,一种黑暗中的神秘。”f白天是正常理性的世界,诗人打着领带,穿着西装,俨然成功者的姿态,茫然而辛苦地奔波在职场之中,时刻感觉到莫名的压力不断挤压着自己。“办公室墙体壁立空气安静/第六感觉却捕捉到周围有偷窥的目光/它们阴冷的力量要撕开我的衣裳”,此时“晴朗的天空/瞬间晦暗”。黑夜是属于自己的隐秘的世界,是思想自由飞翔的自我天地,诗人可以抛去外在的伪装,回归真实的自我。夜色覆盖之下可以真实地袒露自我,诗人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操一张古琴,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诗歌《心中刮起真实的风》中,“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操一张古琴/弹出思接天地的心音/琴是素琴/有形而无弦/有韵而无声”。夜晚的灵魂是自由舒展的,“在夜色的覆盖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
按照弗洛伊德学说,人的心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白天,诗人戴着厚重的人格面具,超我严格地压抑着本我的冲动,扮演着成熟职场人的形象,黑夜之中,诗人终于可以卸下面具,压抑的本我得以释放,灵魂获得短暂的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