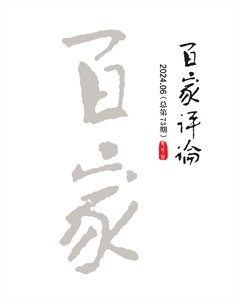内容提要:麦家的《人间信》是一部个体成长的“自叙传”,也是一本咀嚼人生的“沉思录”。作品通过对“我”成长的自叙,对来自原生家庭中的创伤进行了回溯,也对“父亲”成长史中“几乎无事的悲剧”予以了开掘,写出了个体成长过程中来自多个方面的伤害与创痛。个体要成长,需要聚集阳光与温暖,更需走出伤痛与阴霾。最终,“我”在忏悔中担负起了生命的伤痛,走向了生命自觉。
关键词:麦家 《人间信》 创伤 救赎
麦家的小说创作多以“特情”和“谍战”为主,但《人间信》却是一本日常的书,一部成长的书。作品以“我”——蒋春富——的成长为线索,写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也写动荡时代的苦难与不幸,但这些始终都在“我”与蒋德贵的父—子矛盾上纠缠交错,都在“我”对“父亲”与“自我”的反身性审视中聚拢。可以说,《人间信》与一般的家族叙事不同,也与一般的苦难叙事不同,它是一部记录个体创伤的自叙传,也是一部咀嚼人生命运的沉思录。
一、“我”与原生家庭的创伤
郁达夫曾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a这一观点可以用来引领麦家《人间信》的解读。麦家谈及《人间信》的创作时多次表示,这个作品表现了自己和父亲关系的一段隐痛。其实,若将《人间信》与他十年前的散文《致父信》b进行互文勾连,可以见到《人间信》中的情节框架与情感内核与这篇散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再加上作品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人间信》可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但《人间信》是独特的文本世界,它不仅记录着时代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更承载着个体成长的人生印记。这种印记中有阳光和温暖,也有伤痛与阴霾。但对于欠成熟的个体来说,来自原生家庭中亲人的伤害与创痛尤为深切。
在孩子成长期,父亲不仅是物质经济的保障,更是其人格形成期至关重要的资源与典范。但在蒋富春的童年,父亲给他带来的是种种失落、受挫与创伤。“父亲”取名蒋德贵,原本是家族期望他能成为一个“德高望重,荣华富贵”c的人,但他不仅未能拥有人生的成功,反而给家族带来了烦恼和痛苦。叙述者不是以充满敬仰和尊崇的语气来叙说长者的历史,而是在调侃与不屑、愤忿与无奈的语态中来展开“父亲”形象的塑造。“父亲”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他已经远离了乡土的质朴、真诚与厚重。他身上见不到祖父的刚烈、勇敢和血性,也没有续接祖母的勤劳、柔韧和骨气,而是乡村舆论场中令人不屑的“大奶嘴”“老童生”“活鬼”与“日本佬”。当然,叙述者并未完全按照乡土社会对“父亲”的框定来进行演绎,而是也写出了“父亲”的某些过人的禀赋和能力。如“活鬼”名号虽然经时短,但却潜藏着他非凡的绘画天赋;“日本佬”虽然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却表明他有着过人的语言能力。但很可惜,这些全因“父亲”的懒惰虚荣、意志薄弱等原因未曾得到应有的锤炼与发展。最终,他的人设定格为乡村所不齿的“潦坯”上。与上述四个绰号不同,“潦坯”,是蒋德贵人格的标签,也是其人生命运的指向。但从其故事展开的功能与价值来看,“父亲”的成长史与人生史指向的是“我”的成长。在儿童成长期,在自居心理与镜像效用下,孩子总是试图以“父亲”“作为模特儿的人的样子来塑造它自己的自我。”d但奶奶的哭诉与乡亲的戏谑,“我”的亲历,都一一坐实了“父亲”的不堪与恶劣,“父亲”在这里失格与缺位,给“我”的童年人格不仅形成了无法抚平的失落与创伤,更让“我”陷入了原初性自卑与受挫之中。
为了让读者充分认识“潦坯”所包含的意蕴,叙述者不惜反复跃出故事对其进行反复阐释和解说。“潦坯不是恶人,不是混蛋坏蛋,不是狼子野心,杀人越货,伤天害理,十恶不赦。潦坯的意思是多重的,有边又没边,但总的说是指一个人做事吊儿郎当,不努力,做人轻浮,不成器,对自身没要求,对他人无责任”e。“潦坯不是逆子,不是混蛋,不是狼子野心,桀骜不驯,潦坯只是骨头轻,不正经,不记事,守不住做人做事的底线。”f蒋富春的不成器、不长进、意志薄弱,散漫慵懒,给蒋家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他偷奸耍滑,躲在柜子里睡觉而被日寇逮住去做挑夫;他为了一副墨镜的虚荣,差点弄丢儿子“我”;他为了赌博,逼得奶奶痛苦不堪中痛哭不止,几次三番上吊……与这些缺点和毛病相比,蒋德贵最让人无法忍受和原谅的,是他缺乏独立意志、人格尊严与男儿血性——“该硬时怂”。即使是奶奶哭闹上吊,拿出家法——数洋钉来惩罚他,他都不长记性,在父亲一错再错的煎熬下,悲愤交加的奶奶最终离家出走。
父亲让上辈痛苦不堪,让成长的“我”抑郁失落,处处受挫。当别人侮辱父亲时,他以“怎么阻止?嘴长在他们嘴上”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开脱,让“我”为其尊严感的失落感到痛苦;当“我”失去表演解放军机会而伤心时,“父亲”给“我”的却是讽刺与嘲笑,让“我”无法获得家的温暖与关爱;当“我”面对陆军和白毛的侮辱和欺凌时,父亲没有给被伤害的“我”以“温暖的拥抱”,也没有“贴心的宽慰和有力的帮助”,反而给抗争的“我”以蛮横地呵斥和殴打。在痛苦无望与悲愤交集中,“我”将匕首对准了自己,在自己身上划出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也成为了“我”与父亲决裂的鸿沟,也是“我”童年无法治愈和修复的“伤痕”。
“从本质上讲,基本信任与时空在人际的组织状态相联结。”g“家”与“父亲”原本具有的本体性基本信任与生存依赖,在这样的矛盾中离散与消失了。“我”开始离家出走,在干爹家二哥的带领下独自闯荡人生。“我”最终在时代浪潮的怂恿下,走上了“弑父”之路——举报了“潦坯”父亲赌博的罪行,让他遭受了八年的牢狱之灾,“我”也从此彻底走上了叛“家”之路。“我”过早地背负着孤独、寂寞、痛苦与愧疚进入了社会。“我”在远离“父亲”和“家”后,依然难以忘记童年时期因“父亲”带来的阴影和苦痛,但“我”却对生活和家人难以释怀时有愧疚。对辛劳不幸的母亲常怀歉意,参军离开故乡时失声痛哭,得知亲人逝世、离散时有着莫名的悲凉与孤独,在妹妹的劝说下将“父亲”的亡魂从日本接回故乡,百感交集中将老年痴呆的奶奶接回家中……但“我”未曾想到与蒋德贵修复矛盾,也未曾对自己的行为有过质疑与反省……这是“我”的倔强与固执,也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因“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等真正的“爱”h的缺失造成的创伤性心理的过激反应。“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起,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i。
由此看来,《人间信》以“我”与父亲的关系,叙述了一个父子成仇、亲人反目、家庭离散的故事。单从故事情节看,它与卢新华的《伤痕》有些近似,但卢新华将造成这种人间惨剧的原因归结为了时代和社会的疯狂,但《人间信》却并不如此,“我”对父亲的举报,与父亲的决裂,确实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误导和怂恿,但“我”并没有将其视为渊薮,而是将其归结为了父亲的不堪与可供传承资源的代际匮乏,是个体在原生家庭中无从获得“爱”的痛苦和不幸。如果说,《伤痕》旨在揭露社会动乱对青少年灵魂造成的“扭曲”和“精神内伤”j的话,那么《人间信》则更多的是在叙述个体成长时期遭遇的失落与创伤,是人性的阴暗让成长的个体留下难以纾解的痛苦和不幸。
二、父亲与“几乎无事的悲剧”
在“我”——蒋富春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从“潦坯”父亲蒋德贵身上获得认同性资源,他更没有成为“我”人生的陪伴者、引路人,“我”最终只能在创伤与失落中走向了背叛家人远离故乡的流亡之途。其实,作品在展示蒋富春童年人格生成期“父亲”资源的缺席与空位让他造成了无法治愈的创伤的同时,也在叙述着父亲蒋德贵成长的悲剧,只是他的悲剧潜隐而“我”的悲剧显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