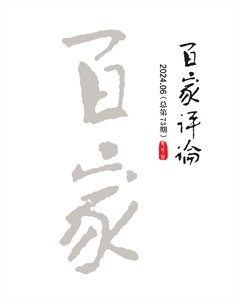内容提要:《天空下》是路也2021年出版的一部诗集,凭这部诗集,路也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诗集《天空下》将日常事物自身奥秘、灵魂和光辉还给事物,释放出“理性认知”拘囿之外的物之灵魂,使得这部诗集获得了惝恍迷离的艺术魅力。“天空下”本身即是一个容载万物的空间,也可看作是可不负载一切的存在之境,这样,天空——天空下——天空下的事物,都纳入在诗中,呈现在诗中,事物互生互证与诗歌互文互释的缠绕间,生成了路也别样的空间诗歌美学。
关键词:《天空下》 路也 空间诗学
“天空下”这个方位性的意象,来源于“天空”的赋予,接驳于地上的事物,有着灵性的自由和实体的依托。“天空下”为路也的诗提供了依托和承载,而“天空下”本身也自成意象。
一、“天空”及“天空下”的诗学意义
路也的这部诗集命名为《天空下》,她认为“天空”摆脱大地上所有烦扰与设限,成为自由的征象:“鹰把自己当英雄,飞至天空的脚后跟/全力以赴地奔向空荡和虚无”。她仰望天空,当目光与日月星云交汇,心底的情绪和经验被激活,成就了超脱于物象的自由感、空荡感、虚无感。
“峪谷”既是天空下的实存空间,也有天空的“他者”意义。诗人记述了自己在峪谷行走一天的生命感知。“两旁崖壁森肃,上亿年记忆/隐含着司芬克斯的脸/抬头望见天空卸下/云朵和深渊”,诗人置身峪谷,惊叹于这里的深邃、邈远、肃杀。被吹落的红叶、孤悬的柿子、晾晒着的玉米,这自然界的一切枯荣有序。“我向峪谷申请/一天往返,在瀑布旁休憩/我向峪谷申请/宽恕之心和遗忘之力//宇宙还在那里,不会被拆迁/想到群星灿烂,想到沧海桑田/所有的痛苦都释然”诗人为现实的繁杂境遇所困所扰,试图从峪谷这里乞求“宽恕之心”和“遗忘之力”,峪谷给了诗人心灵上的巨大触动:人类置身其中的宇宙长久地存在,具有永恒性。而仰望天空看到耀眼的星群在浩瀚的宇宙中闪烁,峪谷在上亿年的岁月中经受了沧海桑田,个人的生命置于其中,只算得上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埃尘。地上的可见的现象转头成为空幻,个人所有的痛苦在永恒面前实在是无足轻重。从宇宙反观自身,诗人由此获得了与宇宙同一的无限感,用无限来观有限,“所有的痛苦都释然”。
“天空”是人类仰望无限的切近中介,也是沟通起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意义的中间环节。“鲜红的一轮,独自狂欢/鲜红的一轮,从大海中昂首阔步地走出/一无所有又无所不有,鲜红的一轮/要升上天庭,要做王//颂歌响起,波涛弹着琴键/霞光快跑,快跑,直到天空的拐角”,这是路也在诗歌《海上日出》中所描绘出的景象:鲜艳、磅礴的红日有着王者的姿态和气场,带领霞光迅速占领了整个苍穹,波涛披着霞光上下翻腾,仿佛在为这一刻弹奏辉煌的乐曲。“面对如此磅礴的上升/我所有的悲伤,都不值一提”,诗人与“海上日出”在目击中获得了互换,以自我观“我所有的悲伤”简直是难以逾越的巨大痛苦,但从日出负海艰难上升的角度来看,自我的悲伤又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
路也的“天空下”具有强大的统摄力量,诗中的所有事物都带上了“天空”的性质。即便是渡口、峡谷、小山、园子,这些天空下的空间以及附着在其上的树林、桃花、信号塔、发电风车等,它们属于大地,也属于天空,这些无限中的有限存在,使得路也诗中的事物获得不被时间、空间所拘囿的永恒性。《太行山》一诗中,“既不属公元前也不属公元后/除了上苍,它什么也不信”,太行山这个巨大事物,在路也诗中成为时间之外、逻辑之外、认知之外的“非人化”存在,它属于天空、宇宙,但它依然信“上苍”,在这里,“上苍”也无非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大和延展。这种无法确然把捉而又端呈活现的事物的把握,赋予路也的诗迷人魅力以及无限阐释的可能。
整本诗集的题目叫《天空下》,容易使人想起“日光之下无新事”的古老训导,而路也却要倔强地写出生命新质、生活趣味。在时间的痕迹上,在万物静穆中,生命的尊严就是诗的尊严,诗的自由也是生命的自由。
二、天空下存在者蕴含生命整体性
天空下的事物,尽管纷繁芜杂,但在“生命”的意义上,都获得了感知和表达。不论是野菊、桃花、松林、青檀等植物,还是海豚、猫、鹰、牛等动物,都具有生命的浑整性,即使是山涧、露台、海浪、墓地,也带上生命的相关性。路也生于济南南部山区,山上的植物、动物陪伴过她的成长,自然与这些活物有着亲人般情感。她曾在采访中说道:“每当我看到一棵草,向别人请教这种草的名字,对方不知道,却一定要回答‘它叫野草’,我就很生气。这棵草是有名字的,跟一个人一样,有学名、有乳名、有笔名,现在统统叫作野草,那就等于说人类也没必要称呼彼此的名字了,都叫‘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男生’‘女生’‘工人’‘教师’算了。这样做,实在是不够尊重。”a诗人把自己融于万物,把自己当作万物之一,不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待万物为刍狗。重新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路径,不仅是生态视野的调整,更是一种诗歌路径的调整:路也将自然界中的每只动物、每株植物都看作是与人类有着同等地位的存在。这一点在《木梳》一诗中有着鲜明的呈现,“在那里,我要你给我起个小名/依照那些遍种的植物来称呼我/梅花、桂子、茉莉、枫杨或者菱角都行/她们是我的姐妹,前世的乡愁。”诗中把“我”与“植物”的名字互换,不仅体现了物、我在世的互认,还体现了作者诗歌写作的“内向性”——“着力于如何让一个异在的世界成为属己的世界”b。
在《寄自峡谷的信》中,这里的巨石、青苔、水洼都彰显着地球的“伟大记忆”,置身其中,能让人忘却这世上任何烦扰。“峡谷”里有原生的自然,也让诗人抵达自我灵魂深处,找寻到了纯粹的自我之境。诗歌《小山坡》中,诗人在一个寻常的午后仰卧在小山坡,“阳光在我的上面,我的下面,我的左面,我的右面/我的前面,我的后面/阳光爱我”,不仅阳光爱“我”,衰草也爱“我”,整座小山都爱“我”。清风、云朵、蓝天、喜鹊,都令诗人感到欣喜,诗人通过这首小诗,透露出了她在荒野之中寻觅到的自适感、归属感、幸福感。
《落地窗》一诗所呈现出的景象:草木用各类方言在漫谈/一枚黄瓜叶子挡住了/两粒西红柿的仕途/茄子在翻起的领口后面,在斗笠下/憋紫了励志的脸/阳光爱瓢虫,瓢虫爱鹅绒藤/蚯蚓在把地球整改/被花粉蒙了心的蜜蜂/正从一朵栀子飞向一朵茉莉。诗人将黄瓜、西红柿、茄子等寻常蔬菜赋以生命情态,展现出炎炎夏日园中的蔬菜被清水浇灌后的蓬勃向上的生长,生动鲜活地对园中小虫的动作予以用情的凝视,以幽默的笔触书写它们的活力,使得这些动植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小小躯体中所蕴含的巨大生命力也得以彰显。
芦花是我国北方秋季水边上极其普遍的一种植物,它们常常成片出现,将辽阔的原野打造成白茫茫的一大片。《芦花》一诗对一支支芦花给予关注。它们在秋风中飘零,那么孤独,大风无情地吹刮,芦花们却像在迎着风奔跑,它们是这原野中孤独的逆行者。“停顿,弯腰,倾倒,伏倒,朝同一方向归顺/它们仿佛在奔跑/不但没有成阻力,反而加快了风速”,这既展现出满地芦花的坚韧,也呈现出了生于荒野的植被们生生不息的品格。
路也在对于动物的关怀中,获得了异在世界的属己存在。在《母亲节》一诗中,关注到了一只流浪猫“阿花”:“多日不见,亲爱的阿花/你走过篱墙,步态比先前雍容/全无去年冬天雾霾里的幽怨//四只毛绒球跟在你身后/在豆棚瓜架下欢快地滚动/其中两只已经开始/练习爬树”。相隔一个春天,旧相识阿花已经发生身份上的变换,成为了母亲,它在流浪途中,未因自身的弱小困于求生,而是“没有耽误青春”,完成了生命的繁衍。世上任何一位母亲,都没有“容易”二字可言,诗中写道:“儿女跟随你去流浪/踏上伟大征程,在通往自由的路上/风雨兼程”。阿花今后要继续承担作为母亲的重任,在流浪的途中独自照顾后代,栉风沐雨、披荆斩棘,这也展示出流浪猫阿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拥有的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路也的诗歌关注到了每一个或是寻常或是微小的生命,用低伏的姿态,用无我的凝视,在自我与物的灵魂互换中,看见它们之中所蕴含的强大力量,这种生命力量,超越了自体局限,成为一切有生命者的生命力的映现。
三、用“行走”激活“空间”的“属己性”
“在路上写诗”,在空间叠加与时间的重合中穿越,一度是路也写诗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给路也丰厚的精神回报,那就是——诗自己呈现自己。
路也瞩目于渡口、火车站、高速公路、航站楼等,写下了《火车一路向北》《那飞机上的人》《高铁穿过秋天》这种动态的“行走”。自己的故乡、陌生的异乡,历史上杰出作家的故居、墓地和遗迹,都曾留下她的生命驻足和深情的凝视。路也在接受采访时曾言:“旅行能够让久存心底的一些情绪和经验被重新激活,精神的地平线被打开来,生命中潜藏着的冲突和苍凉,会突然被激发出来并得以释放。”c路也的行走,激发起她“潜藏着的冲突和苍凉”,在行走的路途中,因体验改变而重获生命体验和心灵的慰藉。
路也的乡野生活体验,为她留存了许多美好又独特的记忆。她在诗歌《童年的河谷》中记述道:“你出生的房子,石头紧绷/跟踪那些显露和退隐的星星/你上过的小学在栅栏后面/有一个独自的领空/你在池塘边钓梭子鱼的时候/抬起头望见打谷场,场上堆着谷捆/小动物窸窣其中”。岁月变迁,那些在故乡度过的日子,那些如贝壳般绚丽的、有趣的日子也都随风而去了。“唯有被写的动物是幸福的,你离世后/它们继续活着/你的童年完好无损/在这河谷之中,躲过了时间的追缉”,狐狸、鹰、乌鸦、云雀……这些河谷中的生命虽然最终也都会离去,却能够因诗人的诗之言说,获得了永在性,在文字中为它们留下不朽的身形体量。如此,即使时光逝去,也能有事物可以追忆。
写英国一个小火车站《约维尔小站》,写异国层累的历史沧桑《泰晤士河》,写“说梦话只能用母语”《小城故事》,写“欧亚大陆”深处的《苍茫》,这些为路也提供了“陌生化”的空间体验,在此被日常固化的感知活泛起来,即是一种深刻的孤独,如在《小城故事》中以复沓回环的一个声音做结:“在小城,啊在小城/我和我自己在一起”。作为个体的孤独,被这异乡小城照拂,只有“自我”和“自我”的分离感中,才能体味到“我和我自己在一起”。这个异乡的空间,不能提供庇护、陪伴,也因此,才能自己发现自己。路也认为当下文学“却忽视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d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路也在异乡空间中,也体味到自己在一个超越日常的更大的宽慰中,在《空旷》一诗中,最后落脚到“神不在任何地方,又无处不在”。《那飞机上的人》中写道:“那飞机上的人啊,从亚洲开始入睡/在欧洲,在北极上空做了一个小小春梦/一直睡到北美,把大地忘得干净”。诗人不歇地行走在路上,从中获得的经验让她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内心的冲突和困境,也让她的心灵得到了温柔的抚慰与治愈。
“死”是生命意识中的另一个迥然有别于“生”的空间。对于生死观的处理,是一个诗人哲学思考的集中体现。路也出生后,相继经历了外祖母、外祖父、父亲的离世,他们的离开给诗人精神上带来巨大打击。路也曾谈到自己写作的源头是恐惧,源于童年的恐惧,这种恐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外祖母的离世,幼时的她目睹这样陌生、令人恐惧的场面,而这种场面在生命之中一次次地重复,便加深了她对死亡的畏惧。后来,她创作出《心脏内科》《你是我的亲人》以及《下午五点钟》,在这些诗中,她一遍遍地重写疾病和死亡。路也认为自己通过书写这些困境,得以拥有里尔克式的态度:面对、看清、说出、写下……最终是为了超越。诗歌《陪母亲重游西湖》中,诗人能淡然地写下“那时父亲还在,指点江山”“父母围在身旁,我的疼痛里有故乡”,透露出诗人对于亲人的离世难以释怀;而诗歌《永别》中,诗人写道:“在你弥留之际,我就不去探望了/你不喜欢人来人往/我不是医生,也不是牧师/无力回天”。诗人向我们传达了她鲜明的生死观:“每一个人都是将死之人/所有冬天只是同一个冬天”。通过行走、通过目击、通过对“死”在意识上的容纳,这样路也就把异己的空间实现为属己的空间。
诗集《天空下》中,“天空”作为 “天空下”的他者而存在,从而使得 “天空下”所含括的形而下的事物,获得了“天空性”,从而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性质。但路也无意于做一个田园诗人、生态诗人、自然诗人,她真正于直观的兴味甚至都不再是天空下的事物,而是“天空下”作为存在的呈现。在言说的不可言说性上,路也开展了一个当代诗人的真正工作——在虚空中活化出存在的灵魂,不停息地在存在与虚无两岸间不断往返。在“天空”—“天空下”互相映射的空间诗学中,用诗活脱出自我意义的不断消解以及自我意义的不断生成,以此来克服“意义贫困”的时代沉疴。
注释:
ac黄尚恩、路也:《发生在内心里的对话,使人永不寂寞》,《文艺报》2023年1月13日。
b丛新强:《论路也诗歌的“内向性”及其诗学精神》,《百家评论》2017年第5期。
d路也:《我的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