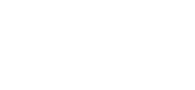本期《啄木鸟》刊发的中篇小说《花木兰》,是我的“派出所长王木多”系列小说的第10篇。事实上,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问世,非常像“命题作文”,从根源上得益于主编和编辑老师前期的选题策划和持续的鼓励推动,而“王木多”之所以被重视,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人设”作为一线执法者,始终孜孜以求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
从故事题材上看,“派出所长王木多”系列小说均可归为警察题材,主要揭示和展现基层公安民警如何灵活掌握政策,合理把握尺度,用真情解构家长里短,用智慧化解鸡毛蒜皮,最大化追求执法的社会效果,送群众宽心温暖,教人们弃恶从善。这一点,是我本人30年从警生涯中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坚守的文学追求。如“罪与罚”的思考:小说《锁麟囊》在弘扬“嫌疑人不归案誓不罢休”的警察执念的基础上着重提出,当一个犯罪嫌疑人主体思想和肉体均业已丧失(思维混乱、四肢截肢)的特殊情况下,还要不要惩罚、如何惩罚?如“性质界定”的思考:小说《打金枝》聚焦乡村久禁难绝的赌博现象,提出如何正确而清晰界定“赌博性质”与“赌气行为”,即“纯金钱的营利性目的”与“物质上的民间义气打赌”的核心差异问题。假如一刀切都定性为赌博去处理,就会丧失甚至有悖于执法的社会效果。小说《对花枪》讲的是一个饱受各种权益侵害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在一次被抢劫的过程中误打误撞得到了一把手枪,然后他以一系列实施侵害的手段来反侵害的故事,深入思考“持有工具直接侵害”与“没有工具隐性侵害”的性质如何界定。在依法打击前者的同时,对于后者的根源性问题更不能无视。
由于“派出所长王木多”系列小说是间断性续篇完成,所以在2018年至今6年的时间跨度中,单篇故事针对当时社会热点的追踪性很强。如2022年刊发的《铡美案》,回应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网络热议,《三岔口》针对近一两年来火出圈的“校园霸凌”,《西厢记》《相见欢》和本期的《花木兰》都对“大时代突飞猛进之下,网络大潮对思想认知未能达到匹配的落后地区造成的巨大冲击”有所揭示。公安题材文学的现实主义属性,决定了我的创作不能脱离时代,必须时刻直面“现在进行时”,针对社会上诋毁、贬损、抹黑甚至破坏我们法治建设的乱象,以笔为枪去“拨乱反正”,去“去伪存真”,这是公安文学创作者理应承担起的一份责任。
此外,“派出所长王木多”系列在讲述法治故事的大框架下,对于偏远小镇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外出与引进”问题,10篇小说或多或少都有所揭示。随着农民外出打工融入大城市生活的经历和经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在他们头脑中形成并固化,受“一切向钱看”庸俗思维的引导,头脑活泛的人开始抓住各种时机以“维权”为由头,为自己谋利。这些社会现象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也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赋予了文学的表达。
总之,我深深觉得公安文学创作除了着眼侦查破案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从而塑造警察形象以外,还要针对执法者如何通过更有效地执行法律从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求真谏言。我的这一点点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个系列小说的时代感、现实性和生命力。
责任编辑/张璟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