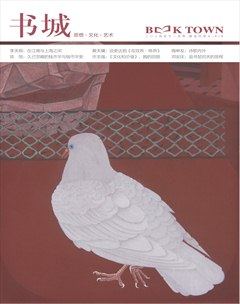著名历史学家沃伦·罗伯茨(Warren Roberts)在《简·奥斯丁和法国大革命》(Jane Auste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979)一书中曾调侃当时流行的论调:女作家小说里有法式落地窗、法式面包和法国厨师,但没有法国大革命。很显然,这是对温斯顿·丘吉尔的隔空回应—后者晚年回忆,二战中他卧病在床,令人取读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对小说中描绘的和平世界感慨系之:“那些人过着多么平静的生活!他们不用担心法国大革命,也不用担心炮火纷飞的拿破仑战争。”
事实也的确如此。翻遍所有作品,不难发现,简·奥斯丁(1775-1817)从未在她的任何一部小说中直接提及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在身后亲友撰写的回忆录及访谈中,这一刻板印象似乎有意无意得到了加强。一八七一年,奥斯丁的侄儿利(J. E. Austen-Leigh)写到,他的姑姑“总是非常谨慎,对任何未知全貌的事情不予置评。她从未触及政治”—在这位传记作家看来,英国乡村的个人、家庭及社区生活乃是奥斯丁全部的世界:“对简·奥斯丁而言,她自己的家庭无可比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微不足道……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宅居的产物。”奥斯丁本人在写给姐姐卡珊德拉的信中谈及自家小说时,也轻描淡写地将其归纳为“乡间三四个人家的生活场景”—这似乎印证了一些批评家的观点,即奥斯丁是“最不具备政治色彩的小说家”。
以《诺桑觉寺》第三章为例。小说男主亨利·蒂尔尼在同自己的妹妹以及女主凯瑟琳·莫兰闲聊时,忽然“岔开了话题,他从一座嶙峋的山石和他假想长在山石近顶的一棵枯萎的橡树谈起,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橡树,谈到了树林、林场、荒地、王室领地和政府,很快便谈到了政治。一提及政治,便容易陷入沉默”—由于有女性在场。按照当时的规矩,绅士不得在男女混杂的场合讨论政治,因为政治是男人的专利。事实上,不仅书中人物亨利及其父蒂尔尼海军上将遵循这一惯例,女作家本人似乎也认可这一惯例。在她的小说里,围坐在起居室的女人通常对邻里八卦更为热衷。
然而,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的勃兴,“不讲政治的奥斯丁”这一传统观点日益遭到质疑。奥斯丁专家索瑟姆(B. C. Southam)解读《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所描绘的乡绅阶层的全面溃败,认为其“根源在于拿破仑战争末期的农产品价格下跌以及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体系的衰颓”;历史学家尼尔(R. S. Neale)在《英国历史中的阶级:1680-1850》一书中更直截了当地点明庄园的财富乃是“基于安提瓜岛上的奴隶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将《劝导》一书视为对英法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崇高礼赞”;玛丽琳·巴特勒在《奥斯丁与思想之战》中则论断:奥斯丁的小说并非单纯记录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而是作者对革命时代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回应;巴特勒以《理智与情感》为例解析奥斯丁的“反雅各宾寓言”,并坚信女作家笔下的乡村生活和革命风波以及思想之战具有“内在关联”。毫无疑问,并非只有拿破仑战争才算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奥斯丁笔下的“英格兰地产主家庭生活的社会史”(黄梅语)同样也值得关注。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奥斯丁时年13岁),不久遭遇欧洲列强干预。路易十六被斩首后,英国第一时间驱逐了法国大使,法国随后对英国(及荷兰)宣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拿破仑攫取政权后,将英国列为头号劲敌,英国在军事与经济方面遭受双重打击,陷入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生存斗争(直至惠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获全胜,迫使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这场斗争几乎贯穿奥斯丁的一生。诚如朱虹先生在《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中所言,奥斯丁把自己的小说称为“二寸象牙上的微雕”,但很显然,她并非不知道在“三四个人家”的琐事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她在自己的一生中目睹“一个帝国建立了(指印度归属英帝国)和一个国家丢失了(指美国宣告独立)”,她的一位亲戚在法国大革命中上了断头台,她有两个兄弟在皇家海军担任要职……对于国内国外的政治风云,像她这样一位感觉敏锐的小说家,怎会无动于衷?借用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话说:“奥斯丁可能不想去理会真理,但是真理很少不传到她那里。”
战争距离奥斯丁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一七九三年,她的兄长亨利加入牛津郡民团并一度担任代理军需官。一八○九年春,奥斯丁前往南安普敦(这里也是《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普莱斯一家的住处),探望时任海军上校的另一位兄长弗朗西斯。此地距朴次茅斯港不到二十英里,风景秀美,但它同时也拥有一个英国海军基地(附近有造船厂)。基地港口架设海岸排炮并修筑堡垒工事,戒备森严,令小说家感觉日常生活“颇多不便”—在她居留期间,这里还是英国海军官兵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拿破仑军队作战的出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