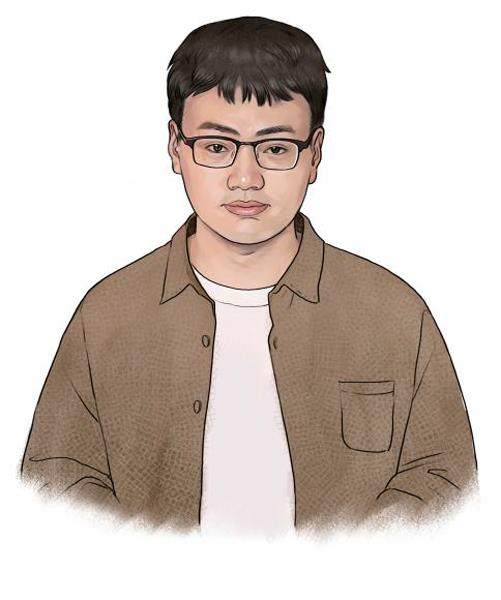
今年9 月,大卫·格雷伯的新书《人类新史》推出了简中版,此时距离他离世刚好4 周年。2020 年8 月的一个晚上,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我的大脑,因麻木的惊讶而伤痕累累。”这是化用帕蒂·史密斯的歌词,末了他又说:“完成了吗?”
彼时人们不知道是什么要完成了,不到一个月,59 岁的格雷伯便因坏死性胰腺炎突然去世。一年后人们才知,这个“完成”,指的是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合作近十年的巨作《人类新史》。这本书英文名《The Dawn of Everything》,意为“万物曙光”,野心勃勃,彻底重写了早期人类的故事。
此前赫拉利等畅销书作家,都把人类的故事建立在线性的进步或衰退之上。比如,智人出现的30 万年间,人类生活在小规模的、平等的狩猎采集群体中。直到公元前9000 年左右,有了农业,于是有了等级制度、官僚体制,有了社会和国家,有了不平等。
但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种人类史观是错误的。近期的考古发现表明,早期人类远非被进化所盲目驱使的自动装置,而是有意识地尝试“各种政治形式的狂欢游行”。
换句话说,他们对政治、对民主和权威的实践,一点也不输开化后的我们。你可能觉得沮丧,人类的政治性,原来这么根深蒂固。但大卫·格雷伯则不然,在他看来,这是更准确的故事,“更有希望、更有趣”的故事。
“我们都是集体自我创造的项目,如果我们不讲述我们的社会是如何从某种田园诗般的平等状态中衰落的,而是问我们是如何被困在如此严密的概念桎梏中,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再想象重塑自我的可能性,那又会怎样呢?”
他始终相信,人类,本该值得一个更好的黎明。
不需要柏拉图们的开智,也不需要孟德斯鸠们的启蒙,打破知识禁锢,人类本身有无限可能。
很多中国读者接触格雷伯,始于他2013 年在《罢工!》杂志提出“狗屁工作论”,但那只是他一时兴起的念头。在他看来,是“管理封建主义”导致“狗屁工作”的出现—老板付钱给员工,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多重要,而是希望通过雇佣下属来感觉自己很重要。这对当代打工人造成了“深刻的心理暴力”。
格雷伯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在于那些被包装成畅销书的写作—很多人都符合这两类要求,而在于他勇于充分阐明自身反对现状的立场:我们的想象力受到了限制,我们神圣的游戏变成了僵化的游戏。作为西方世界难得的左翼思想家和活动家,格雷伯生性慷慨,一生都在为“更自由、更快乐、更平等”的世界而奋斗。
他始终相信,人类,本该值得一个更好的黎明。大抵这就是他离世4 年依然被人们追念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