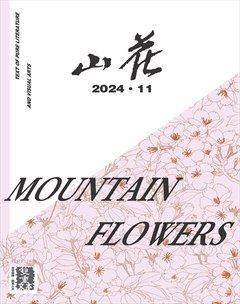1
露丝离婚了。准确地说,七十三岁的她被离婚,结束了与八十五岁的丈夫持续了四十年的第二段婚姻,她挥别后院的五棵柑橘树和遍地多肉,突突地开着二手福特皮卡,搬到了老年公寓。车里除了她从世界各地淘来的旧物,就是一堆形形色色的石头和三只流浪猫。公寓房间小,她每月挤出六百美元,租到小城郊外的一间仓储屋,为那些她前夫眼里的破烂找到了安身之所。
认识她是在去年暮春。
烈日下的荒野,我们八人像长途跋涉的散兵,走着,瞧着,听着。平心而论,风景并不差。黄得耀眼的野芥菜花正开得漫山遍谷,茎高没人腰,远看很像中国江南的油菜花。它们被称为入侵物种,是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传教士带来的芥菜籽的后裔——在美洲新大陆的传教所之间沿途撒种,耐旱且能长两米高的金黄花海可以当路标。
土生土长的野花也毫不示弱,暗紫、橘红、雪白、海蓝,有的是草花,开在脚边,有的是灌木,顶在枝头。花很美很舒展,叶茎却都楞楞紧紧的,带着戒备感,让人想到几千年来与它们朝夕相伴的原住民,脸上身上也是这样的紧张表情。在这美洲大地上,本土植物们没有被大自然淘汰掉,那些以它们为草药为食物的人却不幸地被所谓文明边缘化为稀有物种了。
露丝的嘴一刻不能闲,不时被我们问东问西。她不仅能叫上所有植物诗意的俗称和拗口的拉丁名,还能道出它们的习性。比如,那开暗紫色花的灌木是原住民用来捣碎贴在额头治疗头痛的,她有一次如法炮制,不仅头痛没退,皮肤还过敏起了红疹。“Yuck(恶心)!”说罢她夸张地呸了一口,看似嫌恶,脸上那笑却分明是孩童式的顽皮。
山谷干热。不久前连下过几天雨,一条很清浅的溪水在谷底流着。有一群看不见的人,不急不缓地走在我们中间,男女老幼,身影瘦削,表情无辜凄然,都像在梦游。1928年3月12日深夜,灾难像幽灵无声地降临到洛杉矶这个静寂的山谷。刚建成两年的大坝决堤,60米深的洪水顺峡谷冲泻而下,裹挟着睡梦中的人、畜、房屋、树木、车辆,无情地狂奔了87公里,直到跌入太平洋的怀抱才止歇了躁动。
厚重的建筑残块像搁浅的鲸类,形状不同,姿态各异,不时映入我们眼中,或趴在沟底,或伏在堑边,与那些看不见的人一起,沉睡在近百年的噩梦里——它们都是灾难之夜被冲毁的圣弗朗西斯(Sant Francis)水坝残体。最重的那块约重九千吨,崩裂后在洪水中卷滚着,落脚到1.2公里外的山谷,像为自己找到了坟墓。
“三面环山,修一道堤坝蓄水,这原是好主意。威廉·穆赫兰(Willaim Mulholland)已经建了十八座水利工程,没有一个出过事故。” 露丝嘴唇很薄,说话时皱纹在脸颊上聚拢成大小不一的菊花瓣。她个子瘦小,灰朴朴地立在那儿,像个不起眼的南美移民,可讲话的口气却认真而权威。我忍不住打量她,她头顶的金发盘成贵妇髻,被身上廉价的野外短打衬得有点滑稽。她说这大坝连接的两侧山体太致命,一侧是遇水很易溶解的砾岩,一侧是遇压力会瓦解的片岩。“大坝本身的建筑材料也过于粗糙松懈,泥沙混合鹅卵石,你们从残坝的断面也看到了,那石块比拳手还大,靠泥沙根本hold (固定)不住12亿加仑的水!”
与自学成才的穆赫兰一样,露丝这大坝遗址的历史专家也是自修的,退休老太,无钱无势,十几年来奔走呼号,从市里到州里再到国会,为的是建一个国家灾难纪念馆。那天,是她主动为洛杉矶探险家俱乐部的成员们做导览,我作为唯一的非会员跟着去凑热闹。
“快一百年了,没有任何机构对这遗址做过任何保护,年深日久,这个地方和那些死去的人都会被遗忘。宾夕法尼亚1911年的大坝灾难,死了78人,也没多少遗迹,可人家早就建成了历史纪念地……”大家都安静地听着,望着这个显然很倔强的老人,佩服之余似乎都在心底思忖:换了我,可是没精力也没心思这样做啊!
好几个人迟到了,她亦不恼不急,与早到的在土马路边说笑。一位女地质学家内急,还真按露丝的建议,蹲在车后解决了问题。几步之遥,就有来往车辆呼啸而过。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两院通过,这里终于被列入了国家纪念名录。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日期,你说是不是天意?正好是3月12日,大坝决堤91周年!”她的脸被墨镜遮住一半,自豪之情却一览无余。
“那水坝遇难者中,我猜,有你的亲人吧?”一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探险家迟疑着问。
露丝笑了,露出一口很整齐的白牙,她说还真没有。她和这大坝的渊源早在她出生前很多年就开始了。“我的外祖父是小城柏班克(Burbank)最大的地产开发商,让他骄傲的不是他银行里的存款,而是他的垂钓技艺——他自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垂钓者。他想在这新建的水库钓鱼,但是大坝看守人托尼很不好通融,只允许自己的朋友们在他自己的小船上偶尔为之。那天,我的外祖父母带着我当时年仅六岁的母亲来到这儿观光,很享受地沿着坝顶和翼堤漫步。我外祖母后来回忆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壮观的水库——山峦苍翠,水面宽阔,清澈如湖。经过外祖父几个小时的软磨硬泡,托尼终于答应了下周带他去钓鱼。大家开心地说笑着,没有半点不祥的预感。两天后,大坝成为历史,托尼和未婚妻还有他与前妻生的儿子,成为最早的遇难者,他们的小木屋就在坝底不远的橡树下。”
露丝说她不只一次听母亲叹息着说到那悲惨的一幕,“决堤后第三天,我母亲随她父母再次来到这里……我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叙述中与这里有了关联。六岁时,我也第一次跟母亲到了这里。我相信宿命的安排,我愿意为我母亲心心念念的这个地方做点事。”露丝不必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一路走来,我才知道她的经历颇为传奇。她知道自己有爱说话的毛病,也坦率地告诉我们,因为爱说话她差点儿送了命。二十年前去亚马逊丛林探险,她坐在小皮艇上不停地跟导游打听一种鳄鱼的习性,同伴划桨溅起的水进到她嘴里,她当晚腹泻发烧不止,被带去请巫医念咒,烟薫火燎后,灌了一大桶墨汁般的草药才捡回一条命。
看到杂草丛中一块有黄色条纹的石头,她捡起来,摩挲掉上面的沙土,“多美啊!这是土著人当颜料的ochre(赭石)”,说着迅速凑在鼻子前闻了一下。我笑了,不由得喜欢上了她,去闻喜欢的东西,也是我的小习惯。
成立于1922年的探险家俱乐部自今年起开始接受女性会员,探险家史蒂夫主动为露丝做介绍人。“去过七十八个国家,登过两次喜马拉雅(一次登顶),为加州史上的大灾难奔走,你太够格了!”
史蒂夫与露丝同龄,好奇心让他不时发问,像鱼在吐泡泡。“年过五十才去登喜马拉雅,为什么?”
走了才半小时,烈日下,每个人的衣衫都汗湿了,脚步也不自觉地疲沓放缓了。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来了精神,像羊儿听到了召唤,围拢了些,竖起耳朵听着。
露丝定住脚步,深呼吸了两下,敛笑正色道:“我每天都在想念一个人,那就是我已经去世的母亲。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在怀我之前,她流产了十二次。我十六岁时,她就允许我去西班牙求学,去非洲游历。她说,既然来到世间,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做你想做的事。我曾被USC(南加大)、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录取过,读到半截,没了兴趣就不读了。她并不反对。兴趣让我学会了好几国语言,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还有一点汉语。我想让双脚站在那地球最高点上,就去登喜马拉雅。我不想在某天闭眼时后悔。”有风吹过来,是暖热的。远近盛开的花儿摇曳着,似乎想抚慰烈日下的来客。
露丝说她离过一次婚,与前夫有一个女儿。“她做金融,很有钱。母亲节时来看我,我说,跟我去大坝走走吧。她笑着说不,宁可窝在沙发上玩游戏。我现在的丈夫是退休的西班牙语教授,我每次劝他来,他也是那样笑笑,说不,他宁可一遍又一遍地清洗游泳池,即使一个夏天也没人在里面游一次泳。——走,咱们去看看那块断坝。” 语气里有无奈,脸上却仍是善解人意的笑,她似乎早学会了把锋芒与个性收敛在羽翼下。我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肩,她侧脸冲我眨了眨眼,那顽皮的笑容再次浮现。
2
我们偏离公路,蹚着野草灌木的枯枝,走向一块只露出地面一角的残坝,不时有人蹲下,把那钻进鞋袜的扎人草籽揪出来。那残坝说是一角,实际也有五米高,小山般衬着蓝天,像巨兽的一块风化的骨头。醒目的是两个白色十字架,像两个幼童,并排立在野草丛间,两行黑色的小字,分别在那横条上写着:纪念1928年3月12日此地的死难者,愿他们安息。
十字架不过半米,下面各有一只白色小铁皮桶,插着些假花。“谁安放的?也许是死难者的后人,也许只是毫不相干的人。上次我来还没有呢。”露丝似乎很是欣慰,招呼大家立在十字架边,她用手机拍照留念。那手机让我忘不了,比我远在中国小县城的母亲用的还小还旧。
我已经和老友史蒂夫多次到这山谷远足。遗骸一般的残坝,满山遍地的灌木野花,足有百岁的老橡树……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水泥路面上的那些涂鸦:一只有长睫毛的蓝眼睛仰望苍穹;一束用心拼成的红花被箭射得花瓣凋零;两个并排躺着的人形轮廓……还有些梦呓般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