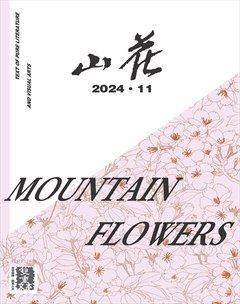内脸与东亚面具
(2024年5月16日)
伊斯坦布尔原本不是非来不可,假如没有俄乌战争,我会直接从圣彼得堡飞往罗马。倒不是不向往伊斯坦布尔,而是我原本并不想跑这么多的国家,想着早点参加完文学活动就可以回国老老实实写作了。因此,我直到买机票的环节才发现问题:俄罗斯直飞欧洲的航线都被取消了。之前肯定看到新闻,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各种封禁,但要不是亲身接触,似乎那些封禁都很抽象。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先回国,再出国;要么去伊斯坦布尔中转,顺便在那里玩玩。我选择了后者,并且顺势决定了一个横贯亚欧的计划。
我购买了土耳其飞马航空公司的机票,很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俄罗斯航空的欧洲业务。我坐上飞机后,发现整架飞机里只有我一个东亚面孔。在俄罗斯这段时间,一直有朋友相伴,这种感受不明显,但从此刻开始,这种感受强烈起来了。
不过,乘务员很友善,年轻的土耳其小哥和小妹,黑色的卷发,圆圆的眉毛,让人想到那些典型的土耳其符号,似乎都是带有圆弧形的,有一股可爱劲儿。
我望着座位前的屏幕,没有什么看电影的心情,便点开本次飞机的飞行航线,进行反复研究。如果没有战争,从圣彼得堡往西飞,到罗马实际上非常近。
现在,我只能垂直往南飞,伊斯坦布尔跟圣彼得堡差不多位于同一个经度。不过,我注意到,向南的过程中还要稍微偏西绕一个弧度,绕开的部分正是乌克兰领空,而且距离基辅很近。万一防空炮弹打偏了呢?不敢往下想了。
飞机上大多数乘客都是俄罗斯人,吃的餐食也是俄餐,他们很安静,小声说话,去往阳光明媚的南方。
伊斯坦布尔机场到了,果然阳光明媚,但我有些忐忑了。
我原本联系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光忠的土耳其朋友。几位朋友在土耳其旅游时跟他结识,他们说他汉语和学识都很好,而且还在中山大学留学过,便热情地将他推荐给了我。我和李光忠在微信上取得了联系,但他飘忽不定,一会儿说要去意大利,一会儿说生病了,最终,在我来伊斯坦布尔的前两天,他说他确实没法接待我了。我原本对他抱有很大期望,这下落空了,我赶紧硬着头皮在携程上摸索,发现有接机和海外订酒店服务,我便下单了。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旅行攻略的人,一方面是以前被人照顾得太好了,走到哪儿都有朋友们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另一方面,我不喜欢过于细节化的旅行安排,只需要知道一个大概情况就行,那种很出名的景点是不可能错过的。我不想把行程排满,我需要在抵达之后还有自由度。这种对未知的期待与探索,让我得以持续保持一种旅行的热情。
在机场,除了我,我只看到了一个东亚面孔。这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不是说中国旅客满世界都是吗?而且,日本和韩国人为什么也没看到?反倒是美国人很多,一听那美式腔调你就能判断。在入境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一行汉字:伊斯坦布尔欢迎您。
这里对入境人员是非常严格的,各色人等汇聚于此,有些人被带到另一侧小黑屋里严格审查,所幸,中国人不在此列。
我等到了我的车,一辆黑色的大商务车,里边的座位是面对面设计的,司机相当于在一个小的驾驶室里,这适合一家人乘坐,而我一个人坐在里边,显得空空荡荡。机场到酒店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车费需要近四百元人民币。
酒店到了,这是老城的一家希尔顿欢朋酒店。入住之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窗外的光线依然明亮,周围很安静,我坐下来休息,能够隐约听到大海的潮声,以及军舰鸟的鸣叫声。
饥饿感来袭,准备按照导航出去觅食。百度地图在这里是可以用的,有中文标识。记忆中,五年前出国时,百度和高德几乎都没法用。我也下载了谷歌地图,但我还是怀着测试国内软件的一种想法。说到这里,对了,在土耳其,抖音和Tik Tok都是禁用的。我偶尔无聊时会刷刷视频,在这里要停止这个习惯了。
走出酒店,向老街走去,道路左边是一片废墟和农田,右边是一面巨大的土耳其国旗,鲜艳的红色,上边是白色的月亮和一颗白色五角星。走过国旗,前方是一个古老城墙的门洞,只容得下一辆小汽车进出。这就是古老帝国的遗产,人们生活在历史遗址的窄门中。
夜色是一瞬间暗下来的,这条老街可不是旅游景区,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生活街,我这唯一的东亚面孔漂浮在夜色中,一个迎面而来的当地人似乎被我吓了一跳。其实我的内心也带着一点点紧张,但他的反应让我忍俊不禁。随后,我不得不审视我的东亚面孔,我不得不跌落到某种边界之内,尽管我主观上并不想这样,但我依然要被他者的目光所塑造。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塑造并非毫无依据,而是来自我实实在在的东亚面孔。于是,我感到人的面孔像是粘在“内脸”之外的面具,所有的人类在文明意义上都有一张相似的内脸,但这指向种族、美丑的面具遮蔽了内脸,形成了矛盾与冲突,也因此制造了一种文明内部的斗争结构。这不同的面具在内部塑造着他者,如果没有他者,我们将迷失在自我当中。
内脸,我多年以前写过以此为名的小说,现在这个题目重新冲出脑际。
我找了个大点的餐厅走了进去,小哥迎了上来,对我用中文说:“你好。”我的东亚面具瞬间消失。
拿起餐单,发现物价比广州略贵,但还可以接受。据说这里的货币(里拉)贬值得很快。我坐在最靠里的位置,面向门口,这样可以观察这个餐厅的情况。我观察着人们,可没人与我对视,我的面具不仅不在了,我整个人都透明了。我总算松了口气,享受肉球之类的晚餐。这里喜欢把甜辣椒焗得烂熟,国内搞成这样要被骂的吧?还有一种白色的软体食物,老板说是用豆面做成的,还挺好吃,我对老板说像中国豆腐,他笑了。
在这里,彼此说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英语,反而毫无压力。
我买单的时候,看到了一大玻璃箱的白色脑子,应该是羊脑,对我这种不吃内脏的人来说,光是看着都觉得不适。
饭后,继续散步,看到了街边拖着小车卖的土耳其烤肉,可惜已经吃饱了。
再往前走,来到一座清真寺下边,正在观察之际,忽然清真寺顶端的大喇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唱经声,让我倏然一惊。很快,我意识到,不仅是这里在唱经,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唱经,那声音悠扬、苍凉又神秘,在城市上空此起彼伏。我赶紧向回走,因为现在不仅是面具的问题,还是灵魂的问题,这个没有经历过宗教练习的灵魂感到了陌生与孤独,想躲进房间里藏起来。
我回到房间里,那声音萦绕在外边,房间像是一个寂寞灵魂的壳子。
人类文明作为整体的历史进程
(2024年5月17日)
我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那种典型的背包客,我总觉得那太刻意了。但人生有时必须刻意,刻意也是一门必修课。
没有了李光忠,还得自己玩。我加入了一个来伊斯坦布尔玩的中国人旅行群,我看里边很多人在吐槽土耳其物价贵,说花了几千里拉都没有吃饱。我在想昨晚也确实花了不少,八百里拉,接近两百元人民币。有人说打车更是贵得离谱,这样一来,我决定徒步逛伊斯坦布尔了。说好听点,叫city walk(城市漫步),这也是近距离考察这座古老城市的好方式。
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另一张中国人的脸。据说欧美人分不清中日韩的脸孔,但中日韩之间彼此看一眼,就分得清清楚楚的,这里面的感受非常微妙。
背上书包,来到了烈日照耀下的伊斯坦布尔老城,我的首个目的地就是声名赫赫的蓝色大清真寺。
老城区路窄,灰尘大,车多,而且全是烧油的,所以空气非常污浊,甚至有些呛人。我这才意识到现在中国的道路上电车变多之后,空气质量确实变好了。我还记得二十年前,我走在广州的马路上,被汽车尾气呛得一直咳嗽。触景生情,今昔对比,变化还是惊人的。
在街上没看到一辆国产车,但看到了小米手机的店。
街上跑得最多的车的品牌,是FIAT(菲亚特),这是意大利的车,我想说一个冷笑话:也许这是东西罗马之间最后的亲密联系了。
我走的这条街全是批发衣服的,生意热火朝天,将原本就狭窄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我不得不从各种缝隙中穿过。我甚至看到有一栋楼全在售卖小孩的衣服,这种感觉让我瞬间穿越回到二十年前的广州。那时候在“北京路”“上下九”或“状元坊”逛街,人潮汹涌至极,好像那些衣服是不要钱的。现在国内线上经济发达之后,连广州这个服装批发的核心城市都日渐寂寞了。
走了很远,终于望到了蓝色清真寺的尖顶,我心底涌出了一股唐僧西天取经抵达雷音寺的情感。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游记》提供的宗教情感体验是极为重要的。我过了马路,转过街角,又看不见大清真寺了。我跟着网络不好的导航继续前进,走上了山坡,忽然,看到了一个小号的蓝色清真寺,通过放在玄关的鞋子推断里边有人正在祈祷,正是因为他们的祈祷,周围显得异常安静。我坐在角落,安静地感受了一会儿阳光,然后继续起身前行。
这时,我明显感到很多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前行,我便知道这个方向没错了。果然,走出这个小巷,就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埃及方尖碑。这出乎我的预料,因此对我形成了强烈的震撼。
埃及方尖碑由粉色花岗岩制成,原本是古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为纪念他的胜利而建造的,位于埃及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门前。公元390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大帝将其运到君士坦丁堡,并竖立在帝国竞技场的中轴线上。这座方尖碑已有近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碑身上刻有当时的象形文字,碑石安放在一个高约三米的基座上,那个基座上有很多小眼,像是子弹留下的痕迹。
方尖碑前方还有一座青铜雕塑,类似两条蛇缠在一起,被称为青铜蛇柱,是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普拉提亚三脚祭坛,建于公元前5世纪,是为了庆祝希腊人在波斯战争的普拉提亚战役中战胜波斯人而建造的。它的顶端原本由三个蛇头支撑的金碗,后来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被盗,蛇头也在17世纪末被破坏,现在只剩下青铜柱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蛇的身体部分。
方尖碑和蛇身雕塑所在的广场是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也被称为古竞技场,是拜占庭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体育和社交中心;而蓝色清真寺就矗立在一边,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重要建筑。
因此,站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来自至少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四种不同文明的冲击。伊斯坦布尔最致命的吸引力就在这里:不同的文明沉积在同一个空间,直接呈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这座城市最初由希腊殖民者建立,名为拜占庭,后在公元330年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重建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里逐渐成为罗马帝国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537年,查士丁尼一世为君士坦丁堡修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使其成为基督教的圣城,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之一。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里曾短暂被拉丁帝国占领。1261年,尼西亚帝国皇帝米海尔八世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它也随之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城市继续扩张,建造了许多著名的清真寺、宫殿和其他建筑,伊斯坦布尔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之一。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衰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首都迁至安卡拉。尽管如此,伊斯坦布尔仍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站在广场上,时间仿佛停止了,然后开始回流……我沉浸在这座城市的历史地层学中。
“朋友,帮我们照张相吧。”一对肤色黝黑的夫妻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认真地给他们拍照。然后,不同的人也都上来请我拍照。东亚面具此刻摘下了,到处都是内脸。我也让他们帮我拍照。我们跟这里的文物一样,尽管带着不同的文化记忆,但到这里都是为了暂时卸载它们,让彼此互相看到。
好了,高峰体检即将来临。我缓步向宏伟的蓝色清真寺走去。脱下鞋子排队,然后小心翼翼进入大寺内部,那种宏阔的空间感与艳丽的装饰令我犹如穴居人第一次见到星空一般惊奇。这么壮美的景点,居然是免费的。
这座清真大寺始建于1609年,由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一世下令建造,以展现奥斯曼帝国的雄厚实力。因此,它的正式名称为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师米马尔·锡南的学生——赛德夫哈尔·穆罕默德·阿加。
清真寺的建造目的是与旁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它。
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后一座大型清真寺,以其内部装饰的蓝色瓷砖和六座尖塔而闻名于世。这些尖塔的数量在伊斯兰教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清真寺内部装饰着超过两万块手工制作的伊兹尼克瓷砖,这些瓷砖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蓝色清真寺因此而得名。富丽堂皇的红地毯覆盖了整个空间,带有古兰经经文的书法装饰着墙壁。
这座蓝色清真寺尽管对游客开放,但它并不仅仅是景区这么简单,它依然是“活的”——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宗教圣地,每天都有穆斯林前来进行五次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