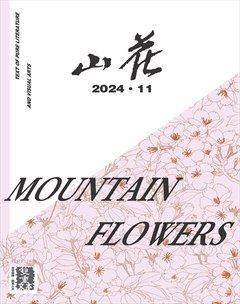“周五晚间,一位女士在北温哥华参加社区园艺活动。一只野生浣熊向她的狗狂吠,这是一只从动物中心领养来的小狗,比浣熊小很多。女士赶忙呵斥,并抱起她的小狗。她感到浣熊爬上了她的后背,又咬了她的腿。其他人赶来……女士被送往医院,缝针并打了破伤风针。这是近期内,本地发生的第二起人被浣熊攻击的事件,上一次攻击发生在几天前,温哥华东……”
兰库太太弯着腰,一条腿跪地,另一条腿半蹲着,正在拾掇一丛新种的绣球花。电台中絮絮叨叨的本地新闻播报声,从开着的窗里传出来。晨光已很猛烈,兰库太太感觉背上晒出了汗。她将小铲收进塑料桶,扶着膝盖,稍胖的身子摇晃摇晃,终于站起身来。
兰库先生戴着橡胶手套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他是个有洁癖的男人,不怎么喜欢和泥土打交道,因此园中的事儿都是太太做。他把洗好的盘子摆在晾水架上,想起去年有郊狼在史坦利公园伤人,后来被捕杀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和黑熊、浣熊、郊狼多年来和平共处,保持着适当的边界。不过,这几年,不少事儿都变了。
兰库太太进屋洗了手,坐在餐桌前,吃先生准备好的早午餐:一碗牛奶泡燕麦、半盘无油炒蛋、奶酪、火腿片、三五只小番茄。她谢了饭,用刀叉切开火腿片,送进嘴里,细细咀嚼。“迈克,”她说,“下午咱们去买点肥料,调绣球的颜色,我喜欢蓝一些的。”她这么说的时候不抬眼睛,声音柔和,嘴角的皱纹一坠一坠。
兰库先生答应着,随手在炒蛋上撒胡椒粉。“去一趟家得宝,”他说,“等我修完篮球架。”
他们有意慢慢吃。兰库太太抬眼看窗外,春风吹过那一片绿莹莹的草地,像一位亲切的朋友,抚摸着正在盛开的杜鹃花和已开败了的石楠。细草尖在树影的边缘,明暗的交界处在闪光。这个花园,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老水手来到餐桌下,匍匐在兰库太太脚上,呜呜发出低鸣。它的头蹭着她的脚踝,尾巴一扫一扫。他们这顿饭吃到了十一点。兰库先生正起身收拾碗盘,兰库太太接到电话,是教会的姐妹打来的。兰库太太没去教会,她们特意问候她。今天是母亲节,每个母亲都会接受大家的祝贺,收到教会赠送的康乃馨。兰库太太从没做过母亲,不是她不想,他们试了很多办法——她认为那是她人生的重大失败,兰库先生不这么想,但没法说服她。他们约定,母亲节这天不去教会。六月份父亲节的那天,兰库先生还是会去。他想表明自己并不在意,愿意为其他的父亲祝福。
兰库太太和姐妹聊了好一会儿。兰库先生听见她们在说:物价涨了,牛肉贵了好多;航空公司改变航道,可能要从本社区上空经过,大家担心噪音……他上厕所时,顺手刷了马桶。然后他去看篮球架,那个架子搭在车道上,常有邻居的小孩儿来打篮球。他没事儿时也会和他们玩一会儿。他昨天发现篮球筐歪了,只能慢慢把它放倒,看是哪里松了。他跪下来,一只手撑在地上,凑近了看。水手跟了来,站在一边。有孩子来打篮球的时候,它总是很兴奋。兰库先生叫它把车库里的工具箱拿来。水手懂了。它嘴里拽着工具箱把手,急急地,好像也在想篮球架子哪里出了问题。
“迈克,你的电话。”太太把头伸出窗外来喊着。兰库先生这才发现,手机仍在厨房里。他不想接,没什么要紧的,真有什么事,会接着打。电话铃声停了,又继续响起来。
是斯图尔特太太,学校校长。她说:“迈克,七年级有个孩子,叫亚当,亚当·黄。”兰库先生的手还没洗,他抽出纸巾擦手,一面嗯嗯点头:“出了什么事?”
兰库太太啜着咖啡,看着丈夫的侧面。他头发浓密,体格宽阔,鼻梁上部有个棱,好像急速下降的山坡上的一小段平台。他听电话时一只手敲着桌子,这表示他有点紧张。她不免多看了他几眼。
他很快讲完了,说:“我出去一下,学校有点事。”“什么事?”兰库太太问。她总是好奇。兰库先生心中想着事儿,说:“篮球架我回来再修。有个学生在皇家哥伦比亚医院看急诊。我去看看他。”他找到车钥匙,发现放倒的篮球架挡住了车道,于是去挪开。走之前他不忘对兰库太太说:“莫丽莎,你今天很漂亮。”莫丽莎笑了,眼角纹荡漾开去——她穿着无袖上衣和短裤,完全没化妆。兰库先生想,回来时要记得买束花。
水手目送着兰库先生的福特车开远了,一直到兰库太太叫它进去。它有一双黑亮的小眼睛。
兰库先生赶到医院急诊室。等候室里人员密集,空气浑浊。呆滞、烦躁的病人或站或坐,护士、医生穿梭而过。他叫住一个护士,问:“这里送来个小孩,他叫亚当·黄,是在里面吗?”护士双手插兜,耸耸肩,用目光暗示他去排队。他说:“警察叫我来的,我是学校副校长。我听说他在里面。”护士和坐在柜台后的另一个护士小声交谈,然后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那孩子躺在病床上,一只胳膊上正在输液。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兰库先生认出这孩子了,是的,他记得这孩子,是个国际学生,平时怯生生的,英语不怎么好。一个黑皮肤的护士进来,用眼神询问他。兰库先生介绍说,自己是亚当学校的副校长,问:“他怎么样?”护士看了看孩子,低声说:“胃肠炎,可能是吃了过期的、腐烂的食物,急性发作。”兰库先生一下子放心了——他曾担心是更严重的事儿……亚当微微睁开眼睛。兰库先生俯身看他,轻声说:“亚当,你好,我是兰库先生,副校长。”亚当羞涩地躲开他的目光,但又转回来看他。“你会很快好起来的。”兰库先生笑着说。
护士调整了输液管,说:“输过液之后,医生说他可以出院了。”护士示意兰库先生和她一起出去,她说:“他打了911,才被送过来。问他家里人,他说他们出去旅行了,也不让我们联系。我们只好找警察,发现他是国际学生,他的监护人一家去了美国。”
兰库先生点头,笑着说:“谢谢你,我来联系他的监护人吧。”然后医生来了,是个头发花白,留着络腮胡的老医生。他翻着手中的病历,飞快地说:“这孩子独自在家,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待着?”
兰库先生给学校秘书格利亚打电话,她找到了亚当监护人的号码。他打电话过去,打了好几次,那边才接通。
“啊?亚当生病了?!怎么回事……”女人的声音,然后是窸窸窣窣的交谈声,他们说普通话——兰库先生去过中国,听得懂一点中文。等他们终于商量完了,换了一个男声,声音很大,他说:“您好,副校长先生。我们这次出来,是有紧急的事情。亚当平时很健康,这是一次意外!我们出门的时候,都和他说好了,吃的在哪里,有紧急事件怎么做。你看,他不是叫了救护车了吗?他买了医疗保险的……”
听说医生希望他们回来,那边又是一阵商量。那男人显然着急了。他说:“我们在洛杉矶,周二下午才能回去,我们有急事……酒店订好了,不能退。”兰库先生只好说:“我可以把他接到我家里去住,但要监护人同意。”
“好的好的。”男人如释重负,“太好了,太感谢您了!”他们很快发了一个书面的授权书来。
这天晚上兰库先生很晚才到家。多年来这是头一次,在母亲节这天他忘了给妻子买花。
水手冲着亚当叫,是友好的叫,那孩子也许还分不清。他身体虚弱,人有点懵懵的。兰库先生领着他进了家里的一间客房,水手一直跟着他们。莫丽莎清理过房间,这会儿已经睡了。亚当紧紧地攥着双肩背包的带子,救护车载他时,他居然还记得带书包,兰库先生想着,不由地笑了。
孩子量过体温,仍有点发热,于是按医嘱吃了退烧药。兰库先生说:“亚当,明天你不去学校了,好好休息吧。”
亚当嗯嗯应着,眼睛仍是不敢直视兰库先生。兰库先生担心这孩子太害羞,问他:“你想跟你父母联系一下吗?”亚当的眼光闪烁,证明他心里起了波澜,然而他飞快地说:“不用。”兰库先生凝视他,他脸红了,解释说:“有时差。”“你确定?”兰库先生又问,“你不想和父母说说?也许跟他们说话,你会感觉好受一点。”孩子困难地摇摇头。
兰库先生拍拍孩子的肩膀,关上门。水手在门旁徘徊了一阵。兰库先生走下楼梯,做手势叫它,它才依依不舍地跟着离开。
莫丽莎并没睡着,她伸出手臂抱抱丈夫。兰库先生有些歉意,说:“亲爱的,我忘记给你买花了。花肥过两天买吧。对不起……这孩子是个国际学生,监护人一家去美国了,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莫丽莎起身,趿上拖鞋去厕所,回来吃降糖药。她吞药下肚,说:“这么小的孩子……他多大了?”“十四岁。”她回到床上,“他们怎么想的,把这么小的孩子……”“那家人去洛杉矶了,说是有什么紧急的事……”莫丽莎翻身,说:“我说他的父母,是中国的吗?”兰库先生感觉困意席卷上来,他把被子盖住耳朵,说:“国际学生一多半是中国来的。我也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但是学校,你知道的,要赚点钱……这算好的了,去年出了更大的事……”他说着说着,就忘了要说什么了。
莫丽莎好一会还没睡着。她自言自语:“不生孩子也不是什么坏事,是吧?”忽听楼上咣当一声,又扑通一声,她睁大眼睛侧耳细听,一会儿又没动静了。也许是那小孩绊倒什么东西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可怜的小孩,这么小就离开父母。如果我有孩子,绝不会这么对他。这么想着,她在心里为这孩子念了祷告。
身边丈夫的呼噜声响起来。他总是仰着睡,张开嘴,起伏有声。她想推他,提醒他侧身睡,别打呼噜,想想他累了,便随他了。
亚当的书包里没有课本,只有一本日志,上面是些自己都看不清的涂鸦。在这间陌生的卧室里,他睡不着,老房子有股味道,闷闷的。副校长的家,房顶比较低,光线不那么充足。家具整整齐齐的,不像苏阿姨家里,房子大得多,家具却一点儿不讲究。白天,亚当鼓起勇气和副校长太太打了招呼,说了几句,早餐都没好好吃,就逃到楼上来了。兰库太太是温和的,但亚当觉得她不怒自威。亚当心里一直盼着兰库先生回家,觉得他更和善一些。
亚当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邻居家的阳台,路上的电线杆;附近都是小房子,院子不大,到处都是松树、杉树;远处有山。他坐回到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快没电了。
这位兰库先生,学生们背地里叫他浣熊先生——他的姓兰库(Ranco)和浣熊(Raccoon)发音很像。亚当喜欢浣熊,它们身量不大,憨憨的,带点儿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