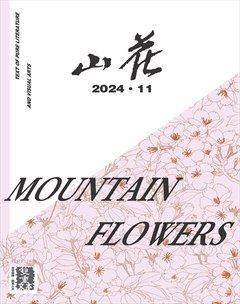疫情结束了,百废待兴。不少单位纳新,我离开了原单位,换到达拉斯上班。在达拉斯,我仍做课程开发。新学校是一所私立的、营利性质的高校,成立时间不长,名气也不大,最出名的一位校友,只是一个参加过美国达人秀的哥们。他的歌唱事业和学校所教的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能说是学校的硕果。不过这里培养的学生,倒是有踏踏实实的薪资丰厚的工作,如护士、助理护士、医疗助理,等等,学校名字不咋样,就业倒是个个实惠。这是多少国内留学生家长不曾想到的。他们哪怕小孩是去耶鲁大学,读个艺术史或者音乐专业,经济前景还不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这是一个美国秘密,当地人都知道,外面的人只认他人拟定的排名榜单,就好比买衣服只看牌子和价格。
新的学校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一应俱全,但更像公司,处境独特。一些非营利性质的学校,大家可以浑水摸鱼。对营利学校,认证机构对它们提着灯笼打着手电拿着放大镜审查所有的经营细节。在政策豁免上,营利性质的高校也是受限制最多的。比如,我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要用到一些外部材料。过去在普通高校做事,可以利用“合理使用”(fair use)原则,在非商业、少量使用、不违反权利人商业利益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使用外部的资料,包括图片,这都不违反版权法,是法律对于教育机构的网开一面。
在我们这种营利性的学校,过去适用的豁免原则,统统失效,连一些共享版权项目的Creative Commons的材料,只要标出了“非商用”(CC-NC),我们都不能使用。大部分时间,我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在老师的PowerPoint中捕捉不符合版权法律的图片和文字。这种类似于版权警察的工作颇为枯燥无味。这种工作,日后经过人工智能的辅助,猴子都能做,甚至可以说猴子就是喝了八瓶啤酒再被人打上一记闷棍都能做。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突然有一天,一个老师向她的领导告状,说我核查版权过于严格,让她的工作没法做。领导乔纳森把我找过去,说:“这事也不能追求完美,你要知道,反正以后再改就好了,你得把项目进度跟上,别的细节一步步跟上。”
这分明是暗示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这不能干。关于营利性质的学校,使用版权作品,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你们不越,让我逾越,哪天学校真被版权人控告了,我来顶包,那怎么行?我告诉乔纳森:“入职的时候,关于版权这一块,大家可是交代得一清二楚的。”
乔纳森说:“当然,我并不是要你去犯规,我只是说在项目管理上注意一下。该紧的时候紧,该松的时候松。你知道,这些课程都不能一下子完美起来,要追求的是结局,而不是完美。你应该听说过,这世上除了死亡、税务,没有什么是无法回头的。”
我想,拔牙和隆乳也该算进去吧,但也没心思和他瞎扯。他的话说得模棱两可,给自己留空间,我则是进退两难。这样下去事情没法干。“算了,我辞职吧。”这句话不由自主地从我的嘴里蹦出来,就如同被噎住后用海姆立克法给激出来的一块辣椒。
这也不全是一时冲动,也算是想法早已在内心翻腾良久,只是寻找合适的突破口而已。这话一说出来就驷马难追了。人嘛,有时候最好的决策,就是念叨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前冲。很多人就是喜欢左分析右分析,最后维持现状,一事无成。
我过去没这么突然地辞职过,总觉得应该有点什么仪式感。警匪片里好警察辞职,通常会把警徽和枪放在上司的桌子上。我于是取下我的工牌,放在他的桌子上,又说了一句:“我不干了。”单位合同没规定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我是说走就走。我收拾了自己的几本书和一些文具,放在一个门口找到的纸盒里,头也不回地搬走了。
这么一放手,扬眉吐气的感觉并没有多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真是拔剑四顾心茫然。那时很多人的家人去世,对生活大彻大悟,有不少人辞去了工作,追求自己想做的事。这情况中国叫“躺平”,美国叫“静悄悄地辞职”(quiet quit)。我想不干事吧,钱从哪里来也是问题。退休还早,还得过几年再说。
我投递了不少简历,但是都没有收获。那时不少老师厌倦了在线教学,转行来做我们的课程设计,不少人年龄比我小很多,薪资待遇要求也不高,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了,更何况我的名字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对方可能还担心要不要请律师帮我办工作签证和绿卡。市场这么饱和,他们并不愁找不到人。
思来想去,我借助过去翻译积累的一些经验,决定做个小的翻译公司。在美国注册个有限责任公司跟玩似的,去市政厅跑了几趟,交了两百多块钱,一个小小的皮包公司就成立了。
在达拉斯这里,华人也不少,再加上人工智能取代了很多翻译的工作,找到业务也很难。撑了几个月,我一单没接到,连房租也没了,只有冒着被联邦税务局罚款10%的损失的风险,取出了部分401K退休金去撑一阵子。此刻真的是危机感爆棚。
大部分时间,我在家会玩俄罗斯方块这种无聊游戏,颓废得很。我白天都去星巴克,要一杯大杯的现煮Pike Place(派克市场),外加一杯冰,在咖啡馆一坐就是一整天,用一种地面以上一万英里的眼神,看着进进出出的男女老少——那些在这里找工作的,谈朋友的,整理财务报表的,做花里胡哨PPT的,还有一些是学生,对着厚厚的教科书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当然,还有一些和我一样在发呆在思考未来的人。不过每天我总有专注的时候,因此也在星巴克干了些实事,比如做出了公司网站,还维护了几个社交账号,希望借此找到客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月的一天,有个医院给我打电话了,有个叫玛丽的女子问我能不能做医疗翻译。我喜出望外,却又不动声色,说让她等等,给我个时间,我去查查日历上有无空档。
要查个毛日历啊?我的日历上白茫茫一片。对方说你明天早晨九点过来,有没有空?有个病人说中文,需要帮助。我说你等等,我去查查。然后告诉她,没问题,别的事情我可以推掉。我明天一早过来。
地址是西南医院心脏科。去那儿见到玛丽,问她是怎么找到我的,玛丽果然说是通过网站找到的。看来那么多大杯星巴克没白喝,做出的网站还是“疗效”显著。
从玛丽这里我了解到,平时医院需要翻译,是通过远程的办法,拿个iPad通话,但是每次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有时候要重新说一遍,很浪费时间。遇到重病患者,貌似需要一段时间治疗的,医院都建议找本地的翻译公司,最好是由同一个人跟踪。玛丽过去联系的翻译公司联系人回国了,联系不上,只好通过互联网找,居然搜到了我的公司,她说她为此十分开心。
我也是。美国主要的翻译需求是法庭翻译和医疗翻译,只要这回做好了,以后前途不是小好,是大好。
病人是个中年人,看上去五十岁的样子,名字叫储梦,挺梦幻的一个名字,但不知为什么就得了心脏方面的疾病。我找到他时,他还在急诊室候诊。我问他是怎么得的这病,他说他是突然发病的,起初只是咳嗽,咳着咳着就出血了。他以为是得的新冠,于是戴上口罩,找到一家CVS药房做了个检查,结果是阴性的。他跟CVS药房的人说要买个咳嗽糖缓一缓,药房的人说咳嗽糖不需要处方,你自己去买就可以,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立马去急诊”。然后他们给了他达拉斯一家急诊室的联系方式。
急诊室听他简单描述,大致明白了一些,没有进一步望闻问切,直接送去做X光、抽血化验、CT扫描,然后告诉他心肺功能急性失常,必须动手术。他的英文还行,但涉及医疗术语比较多,医院为保证沟通充分,是用临时外请的在线翻译和他沟通的。
我到了之后,玛丽叫来了一位心脏科医生。医生看样子是印度裔,皮肤黝黑,但是说起英语来没有印度人常有的那种口音。他和我握手,作了个自我介绍,那姓氏太长,名字倒是短小精悍,叫拉贾。我问叫他拉贾医生行不行,他说没问题。拉贾医生没有时间和我闲聊,直接进入正题,说病人情况危险,需要尽快麻醉动手术。手术之前,需要签知情书,这种大手术毕竟风险很大。他让我问病人有无家属。翻译过去,储梦摇头说,早离了,没孩子,目前就他一个人在美国。医生听我说完后说,有没有紧急联系人?
储梦又说,没有,要不你暂时给我顶一下呗。我想这事事关重大,超过我的职权范围,实在担当不起。储梦眼角竟然现出了一滴泪,再次恳求,我只好答应。我问医生这样行不行,医生说只要病人自己授权,他这边没有问题。但是在病人清醒的时候也不需要,紧急联系人只是紧急情况下才用得着,实在是以防万一。
储梦想了想,问可不可以加我的微信,我说没问题,于是加了他。他说:“我也不知道心脏病手术的成功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有人联系的话,你也好告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