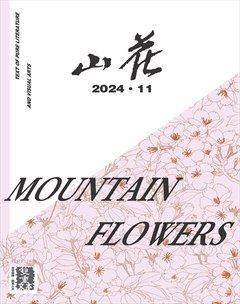地矿家属院的拆迁眼看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两栋没拆完的家属楼也只剩下几户有些执拗的住户,地勘队基地办管主任压抑焦虑了近两年的心情总算得到些许平复。
然而,还没等管主任好好缓口气,这天早上刚到办公室,他的下属小刘就急匆匆跑来向他报告了一条惊悚的消息,说是在拆迁工地上发现了一具白骨,请示他要怎么办。在自己工作生活二十多年的家属院、在自己负责管理的区域发现尸骨,那还了得?管主任决定马上去现场把情况了解清楚。
管主任跟着小刘走出办公室,一阵冷风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往胸前拉了拉大衣。南方的冬天比北方似乎更让人觉得冷,天空总下着毛毛细雨,阴沉沉的。
小刘边走边向他报告情况:听管家堡拆迁工地上的人说,是挖掘机在瓦砾堆里挖出了白骨,现场还发现了一条细小的皮带,奇怪的是周围没发现衣物等其它东西。挖掘机师傅看这些骨头比较纤细,怀疑是一具女尸,已经第一时间向派出所报了案。管主任一边听着小刘的介绍,一边自顾自埋头走路,思索着在自己管理的区域,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怎么就会冒出什么女尸呢?
管主任其实不姓管,大家之所以叫他管主任,听说是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计财科长,由于在审核别人的报账单据时总是细之又细、严之又严,让那些想浑水摸鱼占点单位小便宜的人心里很不舒服,私下里都骂他“管家婆”,甚至有人直接戏称他“管科长”。被人这样戏称,他倒是一点不生气,他的理解是,这反而说明他工作认真负责,于是在别人戏谑地叫他“管科长”时,他也笑呵呵地点头答应,就这样渐渐的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叫他管科长,越叫越顺口,越叫越亲热。以至于后来他调离计财科换了新的部门和职务,大家依然叫他“管科长”,如今他调到基地办当主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管主任”。
想当年管主任大学刚毕业来到地勘队时,一到单位就被安排住在管家堡。当年的管家堡既闲适宁静又和谐热闹,充满烟火气人情味,还笼罩着一层神秘感。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依然让他时常回味。
管家堡并不是一座城堡,而是地矿家属院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由一条两三百米的水泥马路、一排沿路而建的红砖砌成的盖着石棉瓦的小平房、一棵百年古栗树和古栗树下传播开的似是而非的家长里短和奇闻趣事组成。
管主任印象最深的是管家堡那棵古栗树,以及住在古栗树下的人,以及发生在那些人身上的有些离奇神秘的故事。
古栗树究竟有多古老,人们不得而知,没有人去考证过,曾有好奇的年轻人手拉手测量过它的树径,四个身高臂长的小伙儿硬是没能成功合围。大家都觉着自从看到这棵树时,它就一直是这么大,老人们是这样认为,小孩子们也这样认为。
古栗树处在马路和平房的中段,将马路和平房均匀地分成南北两段。处于正中间的平房,也就是古栗树下的那一间,它的最后一个主人,是二十多年前从北方毕业分配到地勘院的高校毕业生南毅,一个纯正的北方小伙,高个儿,方脸,白净帅气。
南毅到管家堡,是地勘院时任后勤科科长老庄领他来的,那是七月炎热的某一天。老庄告诉南毅,为特别照顾外省来的高才生,单位特意将仅剩的几套平房调剂出来给他们住,给他安排的老栗树下这套平房是其中最大的一套。南毅对老庄充满了感激。
老庄走后,南毅便忙碌着收拾房间。他分到的是一套由内外两间房组成的一个套间小平房,里间住人,外间是客厅兼厨房。床、桌椅等一些简单的家具已经提前置办好了,南毅也只是打扫打扫卫生,铺好自己带来的被褥,整理摆放好几本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新家”的布置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收拾停当,南毅拿着脸盆毛巾到屋外洗脸时,认识了他的第一个新邻居,住在他北面隔壁的一个姑娘。
管家堡的生活用水,是地勘队自己打井抽取的地下水,由一根拳头粗的自来水管顺着平房引到住户门口,每隔两户便从主水管上向上立起一根小水管,到齐膝的高度再向左右各分出一根水管,接上龙头便成为住户们的洗漱根据地了,洗脸漱口、洗衣洗菜都在这儿完成。主水管下面是一条水沟,或许是用水的人太多,水沟里的生活余水像小河,常年流淌不息。
一出门,南毅就看到那个女孩正在埋头清洗衣服,水流哗哗地冲击着一个大铁盆,盆里各色衣服随着水花儿上下翻腾。可能是被嘈杂的水流声干扰了,女孩没有觉察到南毅的出现,只顾一边清洗一边将拧干的衣服放进另一个小盆里。南毅犹豫着是否要主动打招呼,看到女孩根本没有发现他,又怕主动搭讪显得冒昧,便自顾自蹲下身打算接水洗脸。他正要伸手打开水龙头,眼前一晃,水沟里有什么东西飘过,南毅下意识地一把捞了起来,竟然是一件绣着黑色图案的白色女式内衣。女孩也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头看向南毅。刚好这个白净帅气的小伙子,正将手里捞起来的衣物递向她。一抹羞红在女孩子白嫩嫩的脸颊散开,她迅速接过内衣,说了声谢谢,便急忙转过头去。南毅愣了一下,他想起白色内衣上的图案是一只黑色的蛾子,镶着红色圆点的黑色大蛾子——竟然会有这么漂亮的蛾子?。
尴尬的气氛使周围一下子变得异常安静,水流的冲击似乎都变成无声的了,他们估计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南毅放好脸盆打开水龙头,女孩那头的水流一下就小了许多,她干脆关掉了水龙头,抬起头来用手撩了撩头发,一颗水珠挂在她黑亮的头发上,随后顺着她的脸庞滴落下来。
女孩看着有些出神的南毅,笑道:“你好,新来的吗?”
“是的,今天刚来。你好。”南毅回答道。他这才看清女孩的脸,一张精致得让人忍不住要多看两眼的脸,高高的鼻梁,清澈的眼睛,白嫩的脸上衬着两个小酒窝,略显羞涩又清纯优雅。女孩虽是弓着背蹲在地上,但女性的柔美线条依然展露无遗。
“是才来队上参加工作的吗?”女孩继续问道。
“是的。我叫南毅。以后还请多关照。”
“我叫秦欣然,左邻右舍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哦,好的,小秦。”
“叫我欣然吧,他们都这样叫。”
“嗯,好的,小秦。哦,不,欣然。”南毅显得有点紧张,额头都悄悄渗出了一层毛毛汗。
“队上没有别的房子了吗?怎么把你安排到这儿了?”欣然若有所思地问道。
“嗯?”
“队上没有给你安排别的房子吗?”欣然补充问道。
“嗯?有什么不方便吗,还是有什么问题?”
“没……没什么,就是那边隔壁住着的棒槌哥偶尔会有点儿吵。”
“哦!”南毅一头雾水,含糊地应道。
第一次见到欣然,南毅有些尴尬,有些紧张,还有些疑惑,然而他的内心是窃喜的——有这么一个优雅漂亮的美女做隔壁邻居,不是谁都有这么好运的。当然他没有丁点儿想要当“隔壁老王”的龌龊想法,只是觉得美好。
后来,南毅从他办公室新同事那儿了解了另一个邻居,住在他南面隔壁的,欣然所说的那个棒槌哥。棒槌哥真名当然不叫棒槌,因为人长得五大三粗,手指头都有小孩儿的手腕粗,走起路来“噔噔噔”把地皮都踩得发抖,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棒槌”。
管家堡的人传言,棒槌有家族遗传疾病,而且好像是传男不传女。让南毅疑惑的是,棒槌这么健壮,怎么看都不像有病啊;他仔细观察棒槌的言谈举止,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之处。
但在管家堡乃至整个地勘队,大家都相信棒槌家族是有遗传病的。他们说他发过病,在老婆带着孩子离他而去之后的那段时间,他时不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头咚咚咚地撞墙,边撞墙还边不停念叨,让邻居们心里瘆得慌。或许这就是欣然不解南毅为何选择古栗树下这个平房的原因吧。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毅心里还是有点发怵的,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棒槌老婆听说是被一个挣了点钱的小包工头给拐跑了。棒槌刚结婚那阵子,还在队上的野外机场从事钻探工作,从年初出队到年底回队,一年在家的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当初嫁给棒槌的时候,棒槌老婆觉得地勘队是事业单位,稳定有保障,因此感觉是满意的。然而后来,地勘队逐渐走入低谷期,不仅收入待遇明显下降,很多技术含量低的岗位开始有人下岗。棒槌倒是没有下岗,只是挣回来的钱少了,又常年在外顾不了家,棒槌老婆慢慢开始有了怨气。
在一次同学会上,棒槌老婆和一个当包工头的老同学联系上了,面对出手大方、穿着时尚的老同学的纠缠,棒槌老婆毫无抵抗之力,一来二去就好上了。棒槌知道后也挽留过,但愣是没留住,婚离了,孩子也判给了女方。老婆孩子离开的那天,准确说是那天深夜,棒槌第一次犯病了。有人听到棒槌屋里传出咚咚咚的撞击声,还夹杂着含混的胡言乱语,像是在咒骂,又像在哀求。
慢慢地,在人们的议论中,就有了棒槌有家族遗传病的说法。
虽然隔壁住着这么一个让人犯怵的邻居,南毅还是很快就找到了心理平衡点,尽管他在心里也暗骂后勤科老庄:背时的老滑头,还说照顾我这个外省人,分明就是欺生嘛!他的平衡点是房间北面的邻居欣然——不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吗?他觉着有这么一个优雅漂亮的邻居,生活都更加绚丽多彩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南毅发现,欣然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女孩,爱养花、爱唱歌,她窗台上的盆栽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欣然一样样告诉他,这叫郁金香、风信子,那叫蝴蝶兰。当说到蝴蝶兰时,南毅敏锐地觉察到,欣然脸上闪过一抹红晕,这让他又想起了初次见面时的尴尬。
欣然唱歌清脆悦耳、甜美动听,南毅最喜欢听她唱《西游记》的插曲《天竺少女》: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南毅曾一厢情愿地认为,欣然是唱给他听的,这一度让他感觉很幸运、很幸福。
南毅这样的幸福感只持续了半年多,无奈的现实就和他狠狠地开了一个玩笑。他回东北老家过完春节返回管家堡时,特地给欣然带了一些北方土特产,一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拎着东西去找欣然。刚到门口,南毅就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在屋里独自玩耍。女孩轻轻叫了一声:“叔叔,你找谁?”欣然从里间探出头,看到是南毅,她先是有点意外,随即就热情地迎上来道:“这么久才回来啊?不上班了?快进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