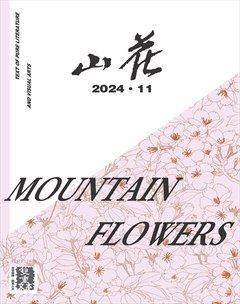1
女人船在外沙桥停泊五日,林弋就醉了足足五日。让林弋醉的不是酒,是坡浪。
“晕陆不晕海的女人。”一说到林弋,外沙桥人都抚着嘴笑。通常只有首次出海回到陆地的人才会醉坡浪,而林弋,出海四年,一直没事儿,自从去年秋天那次返航后,一踏上陆地就犯晕,晕得比旁人厉害,更比旁人久。旁人晕个三五日便没事儿了,她要晕足七日才能缓过劲儿来。而女人船可不待她,只在外沙桥休息四五日便又出海了。这么一来,林弋脚踏陆地的那些日子就都是在醉坡浪中度过的。
外沙桥人都见过林弋醉坡浪的模样,有人啧啧称奇,有人说伤风败俗,有人明着指指点点,也有人偷偷学了她那姿态。可林弋对此不管不顾,照样打横了走,跌跌撞撞的鲁莽,扭扭捏捏的妩媚,眼睛随着身姿的摇曳顾盼生辉,说话还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像是真喝了半斤泡了海马的米酒。有一段日子,外沙桥的姑娘们走起路来一摇三晃,说话也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有心人一瞧就都晓得是学了林弋那丫头。外沙的长辈们对此是隐隐担心,逮着船长英姐就问她何时出海,巴不得林弋立马上了船,离了岸,这外沙桥才能清静。可女人船仍然停在港湾里,像两条沉睡的大灰鲸。
有人曾苦口婆心地劝林弋,你不是醉坡浪不醉船吗?回到船上不就不晕喽?林弋扬起醉眼矇眬的丹凤眼,双手叉腰,母鸡下蛋般咯咯一通笑,脸色一变说道:“姑奶奶我偏不上船,就堵这硌着你们的心,硌着你们的皮。”说罢她摇摇晃晃地离去,还甩了一方帕子,嘴里哼着咸水曲,如果抹上胭脂,倒真像戏台子上唱戏的青衣了。
而林弋远不似青衣那样的柔弱,她是女人船上名声在外的神枪手。那时正是海上的多事之秋,自从去年海上遇见美军飞机后,每次返航,武装部的人都带着女人船上这三十六个女人去练打靶。练归练,女人们心里难免有一个疑问——真要冲突起来,那把土掉牙的枪能顶得住飞机炮弹?疑惑归疑惑,打起靶来也定是不会有半点儿怠慢的。特别是林弋,练得比谁都狠,在海上打活靶她是一打一个准。非但如此,她还能以各种姿势射击,比如从这船过卡到另一船的同时,她还能保持很高的命中率。
外沙桥人常常无法把那个走路东倒西歪的女人和神枪手的身份联系到一起,觉得就像太阳和月亮,南极和北极那样的互不相干。长辈们嘴里夸的林弋和批评的林弋仿佛就是两个人,也许这才是他们能接受的事实。可后辈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无论是作为神枪手的林弋能做出这样的姿态,还是作为做出这样姿态的林弋恰恰是个神枪手,都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
2
林弋以前并不醉坡浪。女人船上的赤脚医生麻婶先前断言她是中了邪,病根是在去年女人船开往越南扁山取水的时候落下的。
“是吓出来的毛病。”雀儿很肯定地说。
“可也没见其他人吓出这毛病。”振西提出疑问。
“一起去取水的还有我呢,我就好好的。”二妮翻了个白眼。
“你还好好的?是谁发誓说宁愿变成一头海猪也不再去白井了?”雀儿抚嘴笑。
“这前有飞机炮弹后有鬼的,换成你也会惊死去。”二妮猛一跺脚,不乐意了。
最后还是英姐作了总结性发言:“林弋那丫头身体没毛病,是心病。”大家都点头表示赞同,而至于心病从哪来,一时半会儿又都说不清楚。
去年夏末,女人船去公海邻近越南扁山一带捕鱼,那次随船带去的淡水用完了,只好到一个叫白井的水源地取水。当地人都在那儿取水,从凌晨四点到晚上十二点都排着长队。女人船想去取淡水只能错开时间,在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前往。当地人迷信,在那几个时辰里是不会去的,说阴气重,生人斗不过野鬼,去了怕是魂儿都要被收走。怕归怕,淡水还是要取的,船上没水可没法子生产了。于是,那夜十二点刚过,七个女人便坐着小船靠了岸,只留下阿水看守小船,其余六人分别挑了两个水桶,步行四十分钟到白井去。必经之路全是坟山,腐尸味一阵比一阵浓。女人船上的女人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来了都不怕,唯独怕鬼。那夜里黑不溜秋,只有远远近近的鬼火一闪一闪的,似紧跟着她们行进。阿细姐胆子最小,一路脸色发白,牙关紧咬。她想说回去吧,可这话又实在说不出口,只能硬着头皮夹在几人中间机械地朝前走。
白井那一带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山,接水处被坟头包围着,要仔细绕开才能来到那地。出水也是小得稀奇,女人们蹲在地上一瓢一瓢地接,等接满了六桶就由三个女人先挑回小船,等她们再返回时,另外六桶刚好装满。这样两组对着走,节省了不少时间,但要挑满一船的水,时间就快到凌晨三点了。
那夜的水仿佛要捉弄这帮女人似的,水流越来越细,到最后一担时,半天接不来半桶。有一组人先行离开了,估摸着早已回到了小船,留下来的一组人是林弋、二妮,还有阿细姐。
二妮等得心里发毛,使劲儿踢了那桶说:“这水比尿还细,接个鬼。”
阿细姐脸色一变:“你说啥?”
二妮气头上又恨恨地哼了句:“接个鬼!”
阿细姐惊恐地看向二妮身后,那里闪烁着几团鬼火,像是越来越靠近的样子。她结巴了起来:“阿妈说夜里说不得那东西,你一说它就要来,还会一直跟着你。”说完尖叫一声抱头蹲了下去。
二妮被阿细姐此举吓得不轻,想回头看又不敢,麻麻刺刺的感觉从头皮一直蔓延到脚趾。“听越南船上人说这一带还有老虎。”二妮本想转移话题,不料却哪壶不开提了哪壶。
只听阿细姐拉着细细长长的声音哭了起来:“我怕鬼又怕老虎——”
“听说老虎还吃人哩,刚刚走过来时路边还有白骨。”二妮没心没肺地又补了一刀。
阿细姐干脆坐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哭声不大,却传出老远,但又像忽然遇了山,钻了谷,又或是被某个庞然大物给一口吞掉了似的,戛然而止。二妮上前一把按住阿细姐的嘴,说:“你作死啊,要真引来老虎,把你丢给它吃了换我们走。”
阿细姐气急,用力挠了把二妮的手。
二妮吃痛,回了她一巴掌。
俩人掐在了一块。
一直没吭声的林弋呼一下站起身,拎起水桶,把里面刚接到的小半桶水往她俩身上泼去:“要打回去打,离姑奶奶远点儿。”
俩人冷不丁被浇了一身湿,想发作,看看林弋铁青着的脸又不敢。
“我们走。”阿细姐似忘记了方才还在和二妮干架,扯了扯她的衫尾小声说。
二妮不作声,身上被浇了一身湿,心里赌着气,扁嘴瞪着林弋。
“都给我滚,省得在这丢人现眼。”林弋有些不耐烦。
阿细姐这时候也顾不得义气了,小声撂下了句“那我们先回船上等你”,便拖着二妮,挑起水桶飞快地往回走了。
3
白井一带静悄悄的,只有细细的水流往下淌时发出的微弱声响,但再微弱的声音在这夜里也显突兀。林弋警惕地盯着四周,耳朵敏锐地捕捉任何一个异样的声音。
此时水流变大了些,两个桶轮流着被接满了。林弋把桶挑上,原路返回。路上照样有鬼火跟着,林弋想唱歌,可喉咙像锈掉了,出来的声音又细又颤,像哭一般,反而增添了奇怪的氛围,便住了嘴。她绕过一个又一个坟头,碎步疾走,生怕水桶里洒出更多的水。空气里的腐臭味依然很重,她憋着气,怀里像藏有一个秤砣,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来了。
快了快了,凭直觉,离海边越来越近,林弋都能闻到海水的咸腥味了。此时,一道刺目的白光射向天空,把周围照得如白天一样明亮。林弋停下脚步,看向天空,愣了一下。接着她听见了“隆隆”的巨大声响,一个像大鸟的黑色物体向她冲来。林弋惊叫一声,马上蹲下。大鸟从她头顶飞过去,不一会儿又飞了回来,如此反复。当第二颗照明弹射向天空时,林弋终于明白自己是遇上美军的飞机了,霎时间吓得腿软,但越是想跑越是跑不动,双腿像被钉在了地上,肩上还挑着老沉的担子。此时飞机降低了高度,在她脑袋上方盘旋,扔下了一堆什么东西。林弋心中一慌,猜想这是向自己发射炮弹了,便闭上眼,绝望地等待着。等了一会儿,没听见爆炸声,反倒是有什么东西拂过自己的脑袋,也不疼,伸手抓来一看,是一些宣传单。
林弋回过神来,猜想对方也许并不想要她的命,她得趁对方改变主意前赶紧逃。这么一想便撒腿跑了起来,跑出几步,惦记着那两个水桶,犹豫了一下,又回头挑上了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