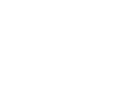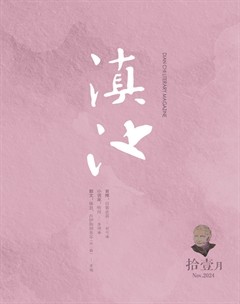大概是在代步车里程超过十万公里时,陈晓宇莫名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不是对这辆千疮百孔的车,而是不断磨损的生活本身。无意义感就像无处不在的汽油味一样,一点火就会烧起来。经常在等待启动的间隙,他会对着前方的车流恍惚起来,回想起一些久远的事,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叠映在车窗上,直到变幻的红绿灯把镜头切回现在。
每天都要经过二环路高架,窗外所有的景物都是无数次路过的,已经从一栋栋具象的建筑褪色成无数个像素点,那么密集的色彩交织,就是连不成一幅完整画面。他可以数清上班路上要经过的红绿灯数量,从前方车流预估出到家时间,与真实结果非常相近。有时他会绕路去接在另一家国企上班的妻子或是在初中念书的孩子,但多数时候妻子和孩子早已挤地铁回家了。原先他们经常下班以后去望京吃烤肉,但自从陈晓宇当上中层主管以后,这点乐趣也被剥夺了,再说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体重暴增,不适合再吃这些油腻的食品。
陈晓宇总感觉不对劲,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夜深人静或酒过三巡时,他跟那些信得过的朋友交流,他们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中年危机。有人建议他去找个姑娘,重新唤回欲望和激情,但被他拒绝了,他并非不渴望新鲜感,而是风险厌恶型的他讨厌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不确定的关系之中。还有人建议陈晓宇趁假期去山里修禅,推荐了熟悉的高僧为他点拨,他加了师傅的微信,对方不断给他发来灵修套餐,根据是否吃斋、念经的种类和数量而收取不同费用,询问其如何选择,“一般而言对于企业家,我们建议你重点学一学《金刚经》”,他突然断了继续学习的念头。
陈晓宇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他在网上下载了SDS抑郁自测量表,认认真真答完所有题,结果是有轻度抑郁的倾向。他不放心,又去人民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拍了脑电图和心电图,主治医生非常耐心地检测完所有项目,告诉他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要学会自我调节。陈晓宇仍然不相信,固执道,他感觉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曾经喜欢游泳,因为体力不支很久没去了,看历史书的习惯被碎片化的手机阅读取代,同学聚会和商业应酬一样难以忍受,就连一度旺盛的性欲也几乎荡然无存。他经常彻夜失眠,记忆力也在持续减退,甚至在路上突然遗忘刚刚打招呼的老领导名字。医生打断他,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建议他去看看中医。后来,陈晓宇辗转几家老字号,望闻问切,没有明确结论,不过开了些安神补脑液。
对此,陈晓宇的妻子林珊毫不知情,当然她能看出来陈晓宇叹气的次数明显增多,吃饭时走神的时刻大大增加,晚上温存的时间几近于无,但她觉得是一种正常人类朝着中老年过渡的自然现象,时间就像引力,缓慢而坚决地牵引着他们的眼袋、皱纹、双乳、脊椎、发际线,以及荷尔蒙水位不断下降,而唯一能延缓进程的办法就是做引体向上,就是克服重力。
她已经开始率先示范。每当陈晓宇回到家,都能看到妻子在儿子以前玩玩具的泡沫地板上,闭着眼睛,把身体蜷曲成一个匪夷所思的姿势。她说她在做普拉提,唤醒体内沉睡的潜能,并通过冥想正念摆脱重力束缚,在无垠太空中漫步。她试图说服陈晓宇加入双修,陈晓宇勉力尝试,但最初的一个拉伸动作就让他闪了腰,疼痛难忍,紧急送到医院。
在病床上,陈晓宇靠着支架躺了一夜,林珊要上班以及照顾孩子,出现一次后就迅速离开。那一天病房里另一位高位截瘫病人转走,只剩下他一个人,安静到可以听见外面大王椰子树落叶的声音。手机经常震动起来,是待办事项的闹钟响起来,提醒他要去开会啦、汇报工作啦、按时吃降血压药啦、参加人事部门面试啦、和孩子班主任沟通学习情况啦。每当一段铃声响起,他会像杀死一个臭虫一样迅速摁掉,心中充满了杀戮的快意。他从未想到平时要处理这么多琐碎的事。
面对一片雪白的天花板,陈晓宇忽然感觉参悟到了自己无意义感的来源——迄今为止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必须去做的事,而他希望做的却是不必去做的事,比如躺在床上,静静看着蜘蛛在天花板上结网,担心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午睡起床后那只蜘蛛消失了,留下一张未完成的网。陈晓宇掀开床单,内外翻看,没有发现虫子,下了床在房间里走一圈,查遍所有角落依然没有它的踪迹。在弯腰低头时陈晓宇扭动了几下腰,已经没有痛感,他感觉恢复情况良好,申请提前办理出院手续。
交完费陈晓宇才意识到病假时间是到明早结束,贸然回办公室没有必要,显得太热爱工作也不太好。这个点孩子正在上课,林姗应该正会见客户,都不必打扰,整个世界暂时没有谁需要他,他好像平白无故多出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半天。
陈晓宇把车钥匙插进孔中,临时决定去郊外的大学城。疫情后,大学加强了门禁管理,不准校外人员进入,陈晓宇和门卫沟通未果,只得转入旁边新建的游泳馆。他记得上次下水还是一年前到国外出差,晚上睡不着觉,下楼到酒店的吧台喝了点威士忌,然后鬼使神差地迷了路,走进酒店露台的无边际泳池游了几个来回。
此刻,大学的游泳池里盛满年轻的肉体,空气中弥漫着酸性的氯水气味,以及碱性的汗水抑或荷尔蒙气息,中和成无色无味的欲望。按照医生的嘱咐,今天陈晓宇本不该下水,但他还是忍不住换上一次性泳裤跳进池中。他没敢动弹,抱着浮力圈漂在水上,旁边不时有练习蛙泳的学生扑哧出巨大的水花,溅在他脸上,还有不耐烦的泳客示意他去初学者的赛道。
陈晓宇躲到角落里,无意间看到一个身着蝴蝶泳衣的女孩,刘海从泳帽中斜逸出来,有点像李璐。水波一阵摇晃,四面的白色瓷砖仿佛在坍塌,她没入水中,消失不见了。
陈晓宇突然决定抛开浮力板,深吸一口气,猛扎入水中,果然肌肉记忆还没有遗忘,手足自动配合往前跃进,把那几个练习的学生看呆了。在蓝色的水波下,他感觉自己看到了李璐,或是年轻二十岁的她,就在不远的地方疾驰而过,白色的大腿分开海水,就像鲸鱼分开阳光和阴影的边界。他随之转入深水区,越游越快,就在他沉浸于喜悦之中时,突然感到腰部传来刺痛,呼吸和游泳的节奏就乱了,身体开始往下沉。陈晓宇呛了几口水,缺氧的大脑瞬间空白,只剩下活着的原始欲望。一切都是在几秒钟内发生的,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在触底时猛地蹬了下地板,双手朝上挥舞,终于抓住了那根泳绳,把自己捞了上去。
狼狈爬上岸以后,陈晓宇跪在地上吐了一阵呛水,他看到周围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好像是在嘲笑他故意逞能露了洋相。那个女孩也从人群中穿过,一边擦拭头发一边瞥向这里,露出湿漉漉的侧脸,他看清楚了,她的下颚上没有痣,她不是李璐。
陈晓宇匆忙裹上毛巾冲向更衣室。
回到车上,依然处于惊心动魄的状态。陈晓宇没有着急发动车,而是打开微信,搜索李璐的名字,结果显示该账号不存在。他忽然想起她的昵称“鹿妞”,终于在若干奇奇怪怪的备注名中找到她。两人的聊天记录停留在五年之前。那时李璐来北京出差,顺道参加校友会活动,两人在过道上意外撞见,匆匆加上微信,但没怎么聊。回去以后,李璐莫名其妙发来一条消息,你读完《百年孤独》了吗?陈晓宇想了好久才记起那是李璐上学时借给他的第一本书,在天桥下旧书摊淘到的九十年代初版书,那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正风靡全国校园,文艺青年人手一本。开头他读了无数遍,老布恩地亚跟着父亲去看冰,吉普赛人的马戏班带来磁铁、望远镜、放大镜,诡异的情节令人眼花缭乱,但怎么都没法读下去,却又不肯承认,所以就一直拖着没有还。当时,陈晓宇没有回复李璐,也许是因为羞愧,也许是因为不愿跟她有更多交集,抑或是不知道如何作答。现在,这个疑问好像是一颗遥远星球发出的光芒,经过漫长时间的跋涉,再度闪烁在他头顶。
陈晓宇突然下定决心,在对话框敲出几个字:你好,我下个月读完就还给你。但他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读完,以及怎么还给千里之外的她。
好像是急于摆脱这些疑问,陈晓宇立即开车往家里赶。刚好是在晚高峰到来之前,开得比往常更为顺畅。进入市区后,他把车窗摇下来,大风呼啸而过,感觉像是在咬着他的耳根说着什么。
到了小区停车场,陈晓宇犹豫了一会没有下车,上网查了一下《百年孤独》的章节和字数,简单推算出这项任务的工程量,按每天一万字来算,大约要二十多天就能读完,似乎在能力可及范围之内。于是他松了口气,摁下发送键。来不及反悔,那些文字倏忽间从输入框跳到上方的聊天界面,像是一片寂静的湖面倒映出多年前发出的星光。
接近下班时间,分管副总询问陈晓宇是否想去三里屯喝一杯。他把疑问句说得和祈使句一样肯定,因为往常陈晓宇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并立即拿出手机约车。但他未料到这次陈晓宇会明确摇头说想回家。
但陈晓宇没有回家。副总走后不久,他关上办公室门,打开蓝牙音响,循环播放王菲的《百年孤寂》,他不知道要干什么,只是随着音乐摇摆,落地窗上倒映出他模糊的影子,和手持的红酒杯。偶尔有下属来敲门汇报工作,陈晓宇坚决道明天再来。对方怯怯地问,那如果没别的事我就下班啦,陈晓宇提高音量说,你们都赶紧回去吧。
到了平常该下班的点,陈晓宇走出办公室开车回家,拥堵的二环路伴着甜美的美国乡村音乐似乎就没有那么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