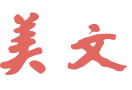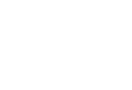不同于母爱如水的细腻、柔和、沟通,父子之间的感情往往克制、内敛、沉默又疏离。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情感社会学语境下,情感表达都是构建父亲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老卫七十大寿的这场喜宴切入,聚焦中国式父子关系中基于沉默与情感沟通缺失的理解错位,关注两代人不同价值观和追求上的认知偏差。老卫的守旧的背后,凝聚着对曾经信任自己、崇拜自己的儿子的怀念,留他在过去的,不是冥顽不化的守旧思想,而是记忆中亲近自己的儿子。小卫的浮夸虚荣背后,是自尊受辱的童年和敏感多思的性格遗留的情感伤痕,他是孝顺的儿子,也是在物欲中迷失自我陷入自证的迷茫者,从而让本该纯粹的父子情变得功利。幸运的是,父子双方固然有着不同的诉求,却又在对彼此的爱中归于一致,最终在无言的体谅与理解中,走向和解。喜宴作桥,勾连父子。其喜一语双关,在长寿之贺,在破迷之醒。
接连一月无雨,日头硬得连柏油马路都要晒化。老卫开着自己那辆二手电动三摩回村的时候,道上半个人影也无。日光下,白花花的水泥路晃得人眼疼。
将车停在麻将馆外,老卫屁股一错,右脚一撑,趔趄着下了车座,拖着两条腿,一高一低地走向麻将馆门口的垃圾箱。拧开盖子,老卫将捞出来的塑料瓶放在脚边,抬腿用力踩扁,最后再弯腰捡起,重新将盖子拧上,将歪瘪的空瓶丢进车厢。今天显然是丰收的一天,三摩车厢里已经铺了厚厚一层。当然,这跟早些年是没法比的。那时候,老卫绕着小县城骑一圈,脚踏三轮的车厢几乎塞得半满,一个瓶子一毛钱,骑一圈回来,也有十几块钱。现在奶茶店开得多了,饮料瓶子反倒少了起来,也掉到了五分一个。以前跟老卫抢瓶子和纸壳的人都不稀得捡了,倒是他,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干瘪的塑料瓶从老卫干瘪枯瘦的手里飞入车厢,与其他瓶子碰撞出低闷的声响。麻将馆里有人走了出来,短袖上卷到腋下,露出啤酒肚,咂了一口烟,缭绕中眯着眼睛看向老卫。
卫叔,大热的天,还往外跑?
没事么。老卫擦了一把额头的汗,视线落在男人右手的雪碧瓶子上。
男人见状,掐下烟,咕咚着将剩下最后两口雪碧喝完,空瓶子递给老卫,揶揄,你儿给你过大寿,你跑外头捡瓶子,小心回去又念叨你。
他念他的,我捡我的。老卫接过瓶子,重复先前的动作,闷着的声音又轴又犟。
老卫因为捡瓶子和儿子起冲突,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小卫有出息,在外闯荡的这些年,赚了不少钱,买了一套大房子之后,就想着带老卫去城里生活。老卫扭捏许久,终于同意,结果去了没几天,忽然自个儿坐大巴回来了,死活不肯再去。一问才知道,老家伙闲不住,每天早晚两小时,守在小区的垃圾点收拢纸壳和塑料瓶。小卫和妻子对老卫在阳台堆垃圾的行为极为不满,扔了老头的宝贝,又带着情绪说了老头几句,老爷子于是轴病犯了,一拍屁股回了老家。
老卫的原话是这样讲的:捡垃圾怎么了?不是你老子当初捡垃圾,能供你念书,你能有现在这能耐?有点本事就瞧不上你老子了?
在村里练出来的大嗓门,隔着通风的窗户将话送到隔壁。没几天,半个小区都知道垃圾区那个新来的老头,住在十六栋八楼,就连小卫出门时也时常被人指点。
这头,老卫嫌弃城里把束,闹着要回;那头,小卫被自个儿爹的离谱之举气个半死,也没拦着。之后的小半年里,两人别说见面了,父子俩电话都没打过一通。但小卫到底是孝子,消气后,念着这些年老卫一个人不容易,找工程队拆了家里的老房子,在原来的地基上起了一栋气派崭新的三层洋楼给老卫住,每个月固定打几千块钱,还特地请了个保姆给老卫做饭。
尽管保姆干了两天就被老卫找理由辞退,但小卫的孝顺周到和财大气粗,还是一度羡煞村里众人。
庆贺新居落成那天,小卫安排人摆了十几桌流水席,请了歌舞团,气派至极。原本事情到这里就算圆满落幕,谁知道饭后小卫喜庆盈盈送客,老卫却在喜棚里和村里另一个捡废品的老太太因为饮料瓶子该归谁起了冲突。小卫闻讯赶来时,两个加起来年岁过百的人已经不依不饶吵了起来。得知事情的始末,小卫心里蹭蹭冒起无名之火,一方面,为老卫直至今日依旧丢不掉的拾荒恶习而生气,仿佛自己这些年亏待了他似的;另一方面,老卫这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子气,更让他觉得颜面尽失。前面庆贺乔迁的流水席有多长脸,此时此刻的争吵就多让人颜面尽失。种种筹备越发像是巨大的笑话,化作巴掌落在小卫脸上。
那点空瓶子能值几个钱呢?连自己指缝里漏出来的零头都够不上。于是小卫大手一挥,将空瓶的归属权划分给老太太,谁能想到,这决定竟是惹恼了老卫,父子俩当场吵了起来。还是村里众人劝着,又提醒老太太赶紧走,事情最终才得以平息。一场喜事,就这么以闹剧般的结尾草草收场。时隔几年,村里人再次想起那次乔迁宴,总难免揶揄老卫的锱铢必较。
比及当初,如今的老卫已经不再是一点就燃的性子了,但在捡瓶子这件事上,他的执拗却一如往昔,甚至有变本加厉的架势。
小卫在外面赚大钱,人家缺你这卖瓶子的几个子儿?要我说,卫叔,何必呢?安心享福少劳累。
男人咂吧完最后半截烟,将烟屁股丢在地上踩灭。麻将馆里有人吆喝着他的名字,男人转身进了屋。老卫从车上拿出夹煤的火钳,夹起那枚被压扁的烟头,丢进垃圾桶。
何必呢?
平时停车的院子,已经满是临时搭起的锅灶和帮工的人,老卫将三摩车停在离家七八米远的一户无人老房前的空地上,思索着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小卫问过他很多次,外人也问过很多次,但老卫从来都没有回答过。于他而言,捡拾废品似乎早已成为本能。
老卫没念过书,因为天生跛着腿,没学过什么手艺,外出打工也没什么人愿意要他。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就是靠着搜寻与捡拾的“功夫”,娶妻、生子,又在妻子病逝后,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在旁人看来又脏又累不是人干的活计,却让他真正活成了一个人。
当院子里垒起空塑料瓶堆成的小山,他就像飘萍忽然生出了稳固又牢靠的根须,成为虬卧的大树,紧紧抓住这片土地。那是他用过往数十年人生历程验证过的通途,是弯下腰身却依旧能挺起脊梁的生计,更是他证明自己还有些许用处的方式。
但遗憾的是,小卫从来不明白这一点。
小卫是坐在他的脚踏三轮车上长大的。那些年的夏天,老卫不仅收废品,还会载着一车西瓜,走街串巷,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一路吆喝。一个个漫长又炎热的夏日,跛脚的男人在翻滚的热浪中用力踩着三轮,他的儿子则坐在瓜上,立志长大后也要和他一样厉害,载一车瓜,从这里到那里,穿行闯荡在没有边际的世界。
或许每个儿子都在很小的时候,崇拜过自己的父亲,他们畅想着成为另一个父亲,成为那个高大的顶起一片天地的英雄。可等到他们逐渐长大,见识到更广阔的天地,就会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男性在年幼的儿子面前,仅有的英雄时刻,也是他们这一生,最辉煌又最短暂的英雄岁月。
彼时的儿子如此纯粹,他以孺慕的眼神崇拜着自己的跛脚父亲,想要成为另一个他。而在这种时候,老卫都会骄傲又心虚,说道,卖西瓜收废品算什么本事?我们小卫以后要干更厉害的工作,成为更有出息的人。
时隔多年,如今的小卫有着人人艳羡的工作和收入,成为村里人激励后辈的别人家的孩子。老卫固然欣慰,却在近来,时常怀念那段短暂又和谐的被儿子崇拜的时光。尤其在他和小卫接连爆发争吵的时候,这种荒谬的落差感和对往昔的缅怀便越发清晰。
久而久之,在这一天,老卫忽然意识到,或许这种鄙薄与不理解,是在多年前的无数个日子里,自己于不经意间种下的因。曾经的他,或许也和如今的小卫一样,觉得捡拾废品是看不到未来与出路的营生。他是废人,这辈子也就如此,但他的儿子不是,他理当去更广阔的天地,有更光明的未来。而当小卫终于功成名就的这一天,于老卫而言,拾荒这曾经上不得台面的举止,忽然便成为他的勋章,成为他多年辛劳不易的脚注。
可他似乎忘了,这并不是儿子的勋章。
摸出常用的旱烟杆,老卫从囊袋里捏出烟碎塞进拇指大小的铜锅按实,打火机点着,从另一头的木杆处吸咂两口,黑金色的小铜锅里红光翕闪,烟雾便从口中吞吐出来,老卫的神色也跟着松弛下来。
停在左手边的宝马车窗倒映出他靠坐在三摩驾驶座上吞云吐雾的样子,头顶扯着嗓子的蝉鸣将老卫的思绪拉远。
这是小卫年初新买的车。这几年,小卫前后买了三辆轿车,曾想着给老卫留一辆在家里当代步工具,但老卫一辆都没开过。没驾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就连坐车他都浑身不自在,更遑论要他开车。
从脚踏三轮到小三摩,老卫有自己满意的座驾。不必被四周狭小空间包裹,寒来暑往,风裹进发动机的喧嚣里,哪怕日晒雨淋,也可以就这样开下去,一直开下去。在渐起的夜色里破风而行,总是让老卫想起年轻时喜欢过的费翔,发旧的短袖钻进了野风,在背后鼓起不息的驼峰,纵然是背着壳的蜗牛,沉重又执着地就奔向不明方向的终途,也可燃烧成冬日里的那把火。
最重要的是,这敞对日月天穹的车厢里,曾载着他的儿子,他的全部。
老卫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小卫恰坐在旁边那辆宝马里。手指夹着烟,手臂搭在外头,一窗之隔,望着老卫坐在三摩上神游天外的身影。
临时出了趟门,小卫也就比父亲早回来十分钟。全因下车前接了个电话,一来二去耽搁了,这才一直坐在车里。光鲜的人并不时时刻刻都光鲜,这一刻,他需要独属于自己的一根烟的时间,而不是谁的儿子,抑或某村的能人。正如此刻的老卫宁肯被热浪包裹,汗涔涔地抽一锅旱烟。
空调无声地吹着,隔着一扇升起的车窗,小卫望着另一端的父亲。儿时高大挺拔的背,如今早已佝偻蜷缩,仿佛被晒得蜷曲的树枝,精心裁剪的衣服也穿不出好形。三摩车厢里铺着一层被踩扁的塑料瓶,这是父亲一贯的手法,极省空间。早些年的时候,他也曾跟在父亲身后,捡到一个空瓶便激动地上前邀功,然后有样学样,将那些瓶子里的饮料倒掉,踩空,拧盖,丢入车厢。
从脚踩三轮到三摩,他的童年,似乎就是在这样无所庇佑的车厢里肆意抽条,也在这满车的塑料瓶和纸壳中渐趋沉默。年少的人最是敏感脆弱,在听不到那些非议的时候,他也曾向往着和父亲一样,载着一车西瓜在风中驰骋穿梭,回家前再将卖掉的塑料瓶子和纸壳换两根雪糕。可当那些取笑入耳,曾经飞驰的痛快便被父辈不甚光鲜的谋生方式取代,不知不觉化作锋针将少年的自尊戳破。同学异样的眼神,使他在每一个散学的下午,保持高度警惕,以避开父亲在校门口的接送。那个跛着脚的,每天踩着三轮车捡垃圾的男人,那个堆满了塑料瓶的院子,如同一张破烂的网,将他裹得窒息。
直至多年后,他在外面的世界闯荡出一片天地,那低埋胸前二十余年的头颅,这才慢慢抬了起来。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一次次招摇的返乡,一次次街头闲聊不经意显露的骄傲,终于让人们看向他的眼神,变得艳羡又敬畏。可那也仅仅是对他。对一个脱离了乡村,终于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的男人的尊重。至于他的父亲,身上却始终褪不去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卑微与佝偻,洗刷不掉泛酸的汗渍和令人嗤鼻的穷气与滑稽。
这让小卫感觉到挫败。于是他推倒旧屋,盖起村里最好的洋楼,享受着那一道道目光里的钦羡与嫉妒,却万万没想到,会在父亲愚昧又执拗的穷酸小气中,沦为新的笑柄。似乎在他振翅一跃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总有人会以一种极为可笑又离谱的方式,将他从那一道即将跨越的高坎上拽下。
而这一次,这个人,是他的父亲。
他试图理解老卫的艰辛与坚持,但始终窥探无门。就像他不理解,老卫分明可以和城里那些老头一样,吃饭遛弯儿看电视,含饴弄孙享清福,为什么偏要去小区的垃圾桶捡那不值钱的塑料瓶;就像他不理解,分明每个月他都会按时打钱回来,老卫却偏要顶着日晒雨淋,去四处翻找那些被丢弃的空瓶和纸壳。
家里的住宅翻了新,身上的衣服也换了新,可包裹在内里的躯壳和灵魂,似乎从来没有跟随这个时代的变化而进步。直到如今,老卫用的依旧是老款的按键机。小卫曾以为他心疼钱,拿着自己用了小半年的手机给老卫,却依旧被拒绝。
我手机好着呢,能接电话能打电话。
你不管。
小卫想,为什么呢?这个他曾经最熟悉的人,似乎在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固守着老旧的生活习惯,将自己困在过去,掩耳盗铃般不肯面对新的一切。可在他记忆中,这个男人年轻时并非如此。他也曾梳过大背头、穿过皮夹克,在卡拉OK盛行的年代,买一支廉价话筒,连上淘来的二手液晶电视跟着碟片里的费翔高歌。
是从什么时候,他们开始争吵不断?又是从什么时候,他们不再如以往亲密,而只剩电话里三言两语的问候,和逢年过节才回来点卯的程式。
燃尽的烟蒂烫得小卫手一哆嗦,他回过神来。
车窗外,老卫将燃尽的烟锅在车架上敲击几下抖空,又用勾勺挖掉残渣,重新将烟锅装好。左脚一点,他近乎趔趄着从车座上下来,需得扶一下车把,才能稳住身子。曾经长腿一跨,就能轻而易举下车的男人,如今仿佛缩了水的衣服,跟记忆中那个高大伟岸的形象重叠,又分离,最终只剩下深一脚浅一脚,跛足前行的佝偻蹒跚。
小卫从后视镜里,目送那道身影远去,又消失。自始至终,这个男人似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就在不远处。就像中学时代,他刻意躲着人群走,想要将父亲甩开,却不曾发现,那个男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红色的喜棚搭在不算宽阔的水泥村道上,二十八桌流水席,占据了整条路,每一张圆桌最中,都摆放着一只摆盘精美的大龙虾,烟酒成双,菜色精致,跟平日里村中红白喜事宴请的规格截然不同。旁边三层小洋楼高大的黑色镂空雕花门上绑着大红的绸带,院子里从前门到二门,挂着两长串鲜艳的红灯笼,村里来帮衬的男劳女工在掌事人的调度下忙碌着。锣鼓队的喜乐一起,鞭炮齐鸣,直冲天灵盖的唢呐声瞬间盖过盛夏的蝉鸣,伴随着上百响此起彼伏的烟花冲天窜去,在半空炸开看不见的绚烂裂缝,为正午的烈日灌入一股躁动的、激越的岩流。
恹恹无神的村子被唤醒。
筹备许久的寿宴终于开始。
焰火、鞭炮的噼啪炸响,持续了足足五分钟,直到半人高的蛋糕被推上喜棚前精心布置的铺着红毯的舞台。
老卫穿着新衣局促而坐,小卫牵头,带着晚辈们依次上前祝寿。席位上、舞台前,两三百道目光齐齐看来,让老卫前所未有地紧张。台上台下离得远,唢呐与鞭炮声中,他听不清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说着什么,只看到那些人的嘴巴在动,烈日下,仿佛有无数条虫子在他身上蜿蜒攀爬。他无意识地扯着衣角,越发显出肩背的佝偻嶙峋,直到司仪撞了撞他的胳膊提醒,老卫这才回过神来,从旁边的托盘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一个个分给这些儿孙后辈。局促拘束的举止,引发又一阵哄笑。
台上的时间漫长至极,当司仪把话筒递给老卫,让他讲话时,他张着嘴,讷讷好一阵,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后脖颈处,新衣服衣标锁边位置传来的刺痒感吸引,他想伸手去挠,却又觉不妥,只能来回转脖子,最终吐出一句谢谢大家。这样大庭广众之下的发言,对七十岁的老头来说,仿佛一场公开的处刑,比扒光了他的衣服还要让人难受。老卫从没有出过这么多汗,涔涔黏意从额头一路下爬,他连擦汗都忘了,一滴热汗就这么沿着眉骨滑入眼窝沟壑,穿透稀疏短促的睫毛,在眼里浸出酸蜇刺激的痛感。他霎时闭上左眼,皱了脸。台下那无数张笑脸,在唢呐锣鼓的协奏里,汇成一条荒唐的河。河水就像那酸蜇的汗滴,透过皮肤穿过毛孔,给他四肢百骸带来针扎般的刺痛。
直到下一刻,有人拿来纸巾,替他擦去眼窝汗渍和满头淋漓。
手里的话筒被拿走。老卫有一瞬错愕,睁着无事的那只眼看去。
是小卫。
感谢各位乡亲父老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父亲的寿宴。天热,咱闲话不多说,大家吃好喝好,开席吧。
熟悉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入耳中,恍惚的不仅仅是老卫,还有司仪和台上其他提前对过流程的人。谁也不明白,这场寿宴的话事人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但宴席的所有出资都是小卫承担,其他人就算不解,面面相觑过后,自然也不好多言。
小卫,我刚才……老卫颤着声音,以为自己没背出来词犯了错。
跟您没关系。太热了,菜放久了容易变味。小卫无所谓地笑着,替这个分明不情愿,却还是硬着头皮配合着自己完成这场充满虚荣浮华寿宴的男人擦去满头的淋漓大汗。新衣服就是不经穿,瞧这都湿透了,走吧,我跟您一起换件衣服,折腾了一上午,咱也吃饭。
老卫几乎是云里雾里被推着走的。直到坐在席间,还在想着刚才台上的事,父子间多年的微妙相处,让他就算再后知后觉,也清楚自己给儿子丢了面子。但奇的是,小卫好像不甚在意,不仅没有跟他呛声嘲讽,反倒耐着性子给他剥虾、夹菜、倒酒。几杯酒下肚,饭菜的香气夹杂着酒气,在交错的碰杯中,一点点卸去老卫的紧张与不解。
老卫酒量不算好,平时也只一个人小酌两杯,饭桌上难得儿子头一回给自己夹菜,愣怔过后,不免喝多。只是笑着笑着,眼角就泛了酸,直到被小卫拦着,才不情不愿地停了酒。宴席后半场,吃也顾不上,只不住地拍着儿子的肩膀,笑着打量端详,来来回回,只有一句话。
好,好,小卫,我儿子。
嗯,你儿子。小卫笑着应声,在众人不解的目光里,给老卫夹一筷子新上的菜。
宴席什么时候散场,老卫这个醉酒的老寿星早已没了印象。一觉睡醒,已是傍晚。老卫摸着爬起来,正准备去趟厕所,却在起身的时候,看到院子里的光景:
办宴搭建的锅灶早已收拾干净,马路上的喜棚也已然拆除,夕阳下,穿着衬衫的中年男人,站在一堆空瓶子间,拿起一只放稳,抬脚,用力将瓶子踩扁,再拧上盖子,按照大小,在靠近墙角的地方,一只只、一层层垒起彩色的小山包。白色的衬衫已经被夏日的暑热浸湿,小卫却浑然不觉,只专心重复着这个简单,但是又费腰的动作,时不时反手捶两下后背。
直到老卫加入其中。
腰不能猫太低,容易酸。一次可以拆多个瓶子,等都踩空之后,再一起收拢,这样更省力。迈入七十的老卫传授着经验,同时熟练又从容地演示着。
好,我试试。小卫从善如流,听劝照做。嗯,果然这样更方便。
直到听到这一句,老卫才恍然惊觉,自己刚才做了什么,而小卫又在做什么。可是过往的争吵没有传来,瞧不上的嘲讽也没有出现。已经比自己高出一头还多的中年男人,如他所教的那样,耐着性子踩扁一个个空瓶子,再拧好盖子,将这些丢面的东西细心垒叠,像极了多年前那个傍晚,踩扁一只新发现的空瓶,举在手里雀跃着向自己奔来的孩子。
夕阳渐沉,将两道站立又弯腰的身影不断拉长。在地面,在墙角,在映着余晖折射出彩光的塑料瓶里,在夏日的蝉鸣与晚风中,在不断与过往重叠,又走出过往的幻影中,收拢着这场喜宴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