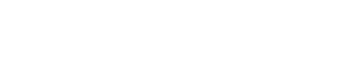采访开始了,大国手在镜头里晃来晃去。
“我在晾衣服。”大国手告诉我。
这种随意,也许是她毕业四年没工作养成的习惯。大国手,哲学硕士,INFJ、B型血、摩羯座、长得像“二次元巨星”大雄,靠写文案、做美工、教哲学课、向朋友借钱维生。她中午12点起床,凌晨三四点睡觉,所以早上经常找不到人。和我聊天的工具是600块钱买的二手苹果XS,家里最值钱的大件是四手摩托车NK250。
她讲话的时候,三只鹦鹉也在插嘴——黄色的叫拉拉,今年5月被朋友捡到后给她养,能吃能拉;绿色的叫开心;蓝色的叫无所谓,当时她正在录制《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无所谓就是她的心情。
作为这季节目第一个出场的新人,她在经历质疑后,偷偷抱持着“老子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大笑圈”的信念,迎来了脱口秀事业的小小里程碑。
在这之前,没考上博士的她筹划跑摩的,贝斯手男朋友骑她的摩托车摔断了手,进了医院要花钱,唯一的生产工具摩托车应当修,但不事生产的男朋友长得有点小帅,“这个‘帅’就是开玩笑”,她特意跟我强调。“生活就像下象棋,保帅还是保车?”“赎车,我得先跑摩的赚钱,跑摩的赚钱,我得先赎车。别人是电车难题,我是摩的困境。”
想破局,就得找工作,“但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而这是她主动为自己选定的道路,“选一个不好找工作的专业,是因为我不想找工作”。她大三那年靠抓住风口做公众号推广,赚过十万块钱,硕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资也有小一万,她不喜欢,干了半个月就跑了。上节目前她做了一番盘点,发现负债5.3万。
人是在一次次拒绝中成为自己的。大国手拒绝过很多机会,诸如一个读博邀约、时薪1000元但理念不合的分享活动等等。正是这种拒绝,让她对人的本心有了些信心。十多岁的时候,她认为人都是目的论的,会设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目标为之前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还美其名曰“自律通往自由”。
年底她就要30岁了,她发现,只要有放弃一些东西的勇气,就会很自由。她尝试着用驾驶摩托车的智慧,自如地掌控生活。她不想被归入任何群体,不想被贴上任何标签,也不是很想完成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化”,“只想行走在主流与边缘中间,好好晃膀子”。
穷,癫,但不想改变
对脱口秀演员豆豆来说,大国手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很魔幻,很少有人很直白地告诉我,‘我很穷,我很缺钱’。”她去喝手冲咖啡,朋友给她介绍豆子是什么香型和风味,她直言不讳说“我没喝出来”,朋友很惊讶,说“一般人都会装一下的”。
初次见面破冰,大国手小小的身体站在长得魁梧的脱口秀演员毛豆身边,看着像他领来的小孩。她安静地躲在角落,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在豆豆的播客里谈起海投入选节目,一张嘴却是大反差:“对面节目也投了,然后没叼我。”
豆豆被震慑了。“他问我是怎么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的,我说这就是事实啊!没工作过,说话就比较直白。”大国手说。
面对节目录制,大国手也有股令人捉摸不透的松弛。她不喜欢“老师”的称呼,对全体新老演员都直呼其名。第一轮她选了理论上选手实力最强劲的“大笑圈”,“来都来了玩点刺激的”;第二轮比赛她对徐志胜,一个写稿的深夜,她穿过节目组的大厅,志胜跟她打招呼说点了宵夜,问她要不要一起吃点儿,她当时“耳朵只听到吃东西,就说好”。
“食令智昏”的她,忘记了自己的交往基本局限在正式录制前的训练营,所以她跟不参加训练营的老演员并不熟络。走到读稿的办公室门口,新人演员无一在场,“好尴尬,我要走进去吗?我跟大家不熟,志胜有没有跟我客套?”
年底她就要30岁了,她发现,只要有放弃一些东西的勇气,就会很自由。
她看到呼兰在往办公室走。“我就上去说,呼兰,需要我帮你改稿吗?呼兰说好呀好呀,我就跟着呼兰进了办公室。很神奇,就感觉我是怎么敢的呀?帮呼兰改稿?”
大国手把一系列理直气壮的“癫”归因于受社会规训比较少。她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如何高情商回复领导”,但她觉得这是一种对主体的压抑:“已经付出劳动价值了,还要你去付出一些情绪价值,把一个简单的交流变得特别复杂。工作上沟通就是你把这个事做一下、我什么时候需要,理解字面意思就好了,多简单呀。”
同时,她也跳脱出了价值判断。穷、不懂咖啡都没啥不好,对面节目没找她,她也没觉得难为情,“就很正常的一个事,也不会让我情感上受伤,我就会直接说”。
豆豆觉得节目像一个巨大的机器,紧张的竞争、对抗氛围也让大国手受不了。当大家在大厅和开放麦间焦虑地往返推敲时,她决定把自己拉出来,逃回成都两天,打“新人团购9块9一个小时”的台球。
得失心时不时会冒出来,冒出来了,就去调节,她早就认清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稿子写不出来,冷场,“就在床上躺着,物理意义上的躺平”,因为她觉得躺着的时候创作灵感比较好,“坐着的时候总会想玩手机,一刷脑子就被影响”。安静地等一等,实在改不出来,就把这个段子扔了,“大不了就换一个”。
她原本设想在节目里能走到第三轮,因为认识的一个编剧告诉她,走到第三轮就能多赚一点,“今年就不愁了”。第二轮赛制公布后,她觉得对手个个实力强劲,“一到家就睡了10个小时麻痹自己”。票数出来,她被淘汰了。受访时,她通过脱口秀赚到的钱还不到一万块,先还了几千块信用卡欠款,“还欠5万多,还了零头,零头还没还完”。
好在她回到成都吃了两天火锅,照旧过着给自己留有余裕的生活:周一写稿,周二上开放麦,周三去兼职哲学老师,周四可能去开放麦也可能不去,以前的周五和周末,别人商演的时候她休息,或者在家看书,中意她风格的观众被吸引过来后,她在线下感受到朋友般的友好,也比之前更放松,“现在演出多一些了,可以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