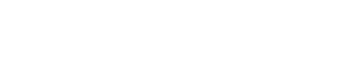去年初,28岁的袁悠悠摸到乳房处有个不痛不痒的肿块,很快确诊了乳腺癌。尽管国内的乳腺癌诊疗已颇为成熟,她还是仓惶地四处求医,想要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
她托朋友、找黄牛,去北京、上海、香港、美国,足足跑了6家大医院,有时同个医院,她还会看不同医生。
袁悠悠说,有的医生让她如沐春风,但也有约一半医生的态度让她不适,甚至几近冲突。关于病情和治疗方案,袁悠悠有很多疑问,但医生们不愿过多解释。
每每碰到背上没有肌肉包裹的区域,Viola还是有些伤感,那是乳房全切及重建手术留下的伤疤。
尽管她的病情相对轻,就医时医护也关怀备至,但在抗癌笔记里,她袒露,“辗转求医的夏天注定会成为我余生的阴影、噩梦和达摩克利斯之剑”。
肖于,曾在记录她乳腺癌康复过程的书里描绘过这种感觉:“治疗过程中,病人通常孤独无助,而治病体验幽暗隐秘,很难描述,很难与人共鸣,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在数以亿计的求医者中,乳腺癌病人是一类典型,她们的经历展示了一种新的医疗需求。减轻痛苦,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可很多新的需求无法在如今的标准化流程里得到回应,而那些难以言说的幽微体验,又真切地加剧恐惧和痛苦,影响更长久的生活。
从健康到舒适,不是一个过分的追求。求医的苦,可以再少一点。
我该相信谁?
看病越来越熟练后,袁悠悠不敢问太多,因为医生会不耐烦。她总结出一条经验,“如果你不是那种听话的患者,他们就会教训你”。
确诊了乳腺癌,袁悠悠很焦虑,看了大量的临床报告、最新疗法,认真到比对两种药物之间,治愈率有什么差距,是哪个研究者做的。她没想靠这些取代医生的经验,而是从中寻找一种确定性,也帮助自己和医生沟通。
很多具体问题,她曾试图跟医生去理性探讨,比如为什么化疗方案里用白蛋白紫杉醇,而不是普通的紫杉醇?
在一位业界大牛给出判断和治疗方案时,袁悠悠对比了另一位权威医生的治疗方案,想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但话没说完,眼前这位医生突然凶起来,直言“我这儿也不想收你”,袁悠悠没敢继续问,觉得委屈。
袁悠悠还有能力在多位医生中间做选择,但她想,如果其他患者花了很多钱、托了很多关系才找到这一位医生,会是什么心情?
袁悠悠需要医生答疑解惑,否则她很难信任地把自己交给一个陌生人,也无法安心治疗。这或许解释了,她为什么辗转找了多位医生,但也因此产生了新的困惑:我该相信谁?
这个困惑贯穿了前期诊疗的大部分时间。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熟悉的治疗方案,但他们往往不愿意解释太多,她只能凭直觉去决定相信谁。
她经济宽裕,计较的倒不是钱,而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她希望和医生一起选择一个好的方案,至少得到医生提供的治愈率这类客观数据。
她知道,国内的医生每天确实特别忙,诊室门口总是挤满了人。但同样是忙,也有例外。有个医生“虽然已经是大咖了,但他都是很耐心,很温和,非常考虑你的感受去跟你聊。医术高,医德好,后来也有口皆碑”,袁悠悠决定信任他。
“如果你是我女儿,我会让你用这个药”
Viola麻利地撩起衣服给医生查体,年轻医生们在出血的乳房上钻研了老半天,还是没找到出血原因,但他们严肃、疑惑的神色又透露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紧接着,他们给更有经验的医生拨通了视频电话,手机镜头直直地对准Viola的乳房。她自嘲已婚已育的中年妇女看得比较开,但那一刻还是尴尬和不适。直到电话那头,传来老医生的训斥“看视频诊断的结果怎么能靠谱”,Viola才得以解脱。
袁悠悠也有类似的尴尬。医生让她把衣服撩起来,对乳房进行触诊,她自己倒不介意,但她为丈夫在旁边而尴尬,毕竟那是个男医生。
从进门诊开始,就有年轻的医生把病历接过去,并且预先做了一轮简单的问诊,等到直接和吴炅医生接触时,她发现基本的问题和疑惑已被解决,吴炅医生只做最核心的工作即可。整个过程非常高效,双方交流也很舒适。
实际上,她们非常理解,能做到不去赋予这些举止任何医疗以外的意义。但袁悠悠想,如果医生能多说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接下来要接触检查”,会让大家有心理准备,也是一种简单的知情同意,免去突如其来的尴尬。
一句话、一个耐心的语气,无关医术,却带来不同感受。
手术前,袁悠悠被医护连着病床推到等候区,除了她,那里还有一排被白布裹着胸的患者。等候区很安静,大家平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几乎没人说话。这加剧了她的紧张。
没想到,反而是从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起,她才放松下来。
“我发现一群医护都站在手术室里迎接我,有人跟我闲聊,特别温和,说你多少岁,老家哪儿的啊……”这些轻松的小问题,把她的注意力从紧张的手术氛围里转移出来,手术室里还放着周杰伦的歌。
医生的关怀和同理心很重要,他们其实有能力用哪怕一句话,赢得患者的信任。
关于术后要不要多用一类药,袁悠悠问过许多医生,那有一定风险,但一位医生在同样告知风险后,告诉她:“如果你是我女儿,我会让你用这个药。”袁悠悠受到的触动极大,最终选择了用。
隐秘的痛苦
治疗结束后,袁悠悠找了心理医生,定期做咨询。
手术没有让她失去乳房,治疗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在旁人看来,她已经恢复了健康,可以正常生活。不过,她依然想和医生去梳理,为什么是我?这几乎是每个患者绕不过的问题,而她只有28岁。
“有医生朋友告诉我,尤其在我这个年纪得乳腺癌的,她见到过的基本上都走不出来。”
和病友交流时,她才意识到,无论她们的病情是轻是重,内心都很煎熬。
乳房全切后,怎么面对性生活?和另一半的关系受到影响怎么办?化疗脱发,难以接受怎么办?担心复发,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很多乳腺癌患者的康复周期长,有些人可能在未来5年、10年,都要与它抗争。这个过程中,抑郁情绪会随时反扑。
这些私密的痛苦,很多病友不愿意也不知怎么跟身边人说,有的一边化疗一边上班,独自去扛。那不单单是保护隐私,还是一种病耻感作祟。
最终,她们在众多不确定性和焦虑里自我纠缠,一如肖于所说,“我的整个世界,全都是水渍,从里往外反上来”。
很多病友喜欢找袁悠悠聊天,这样会让她们好过一点。袁悠悠越来越觉得,患者需要专业的心理支持。
在美国和香港地区求医过程中,袁悠悠注意到,当地的乳腺癌诊疗团队里有心理医生,专门帮助患者缓解病痛带来的心理问题。
缓冲地带
回顾整个治疗过程,袁悠悠接触了很多医生,外科医生、B超医生、CT医生、内科医生……每个医生在完成自己所负责的治疗和检查后,就退出了。
重新去挂号复查,该挂哪个科也没有人提醒,去复查挂号到的医生,很可能完全不认识,又得复述一下病情。袁悠悠感到疑惑,到底谁能对我这个病全程负责?
谁来提醒复查?谁来解答患者的常见疑惑?同样的问题,Viola也想过。
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求医经历,让Viola有过一次特别的体验。
从进门诊开始,就有年轻的医生把病历接过去,并且预先做了一轮简单的问诊,他们是吴炅团队的成员。
等到直接和吴炅医生接触时,她发现基本的问题和疑惑已被解决,吴炅医生只做最核心的工作即可。整个过程非常高效,双方交流也很舒适。
一下子不知道如何确切表述这次就诊体验好在哪儿,Viola想了一下,觉得用“缓冲地带”可能比较恰当。
像吴炅这种全国知名的乳腺癌专家,每天找来看诊的病人不计其数,而他的团队则起了一个“缓冲地带”的作用。
诸如去哪儿检查、挂号收费、术前术后注意事项、复查提醒等问题,Viola认为完全可以让年轻的医生、甚至是他的实习医生或者研究生来做。
患者在每个环节都有关心的问题,比如化疗期间头发和眉毛会掉,能不能纹眉?术后一年,有时候胸还会疼,是否正常?术后能不能运动?
如果医院有这么一个“缓冲地带”,或许很多当下的小问题,即便不用专家出马,患者也能顺畅地解决。
努力向前一步
对于袁悠悠们提及的困惑和需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乳腺外科学术带头人韩宝三觉得:“完全合理合法合规合情,只是怎么把它纳入常规工作,这件事有点困难。”
中国的病人实在太多了,并且每逢大病重疾,患者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医生来看,造成了医疗资源局部挤兑。
面对早期、轻症患者,医疗上要逐步从全切手术过渡到保乳手术,从单纯保命到尽量保证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愈后生活。
韩宝三承认,客观来看,目前人文关怀是欠缺的,很多医生还是以解决疾病的刚需为主。
但他也无奈地举了个例子:国家卫生部规定过,每个专家看诊应该达到10分钟,但病人“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的吐槽还是不绝于耳。
一方面,看诊没有计时,医生实际上可能讲了5分钟、8分钟,病人以为3分钟。更重要的是,病人太多,每个人10分钟,可能最后那个人得等10小时。
尽管如此,“做不到,不代表我们不该努力去做”,韩宝三反复强调医学毕竟是“人”的科学,像乳腺外科、妇产科这类涉及私密部位的科室,更需要人文关怀。
因为医患关系最核心的就是信任。
11年前,韩宝三偶然看中一块格子布,买了回去。他想到,夏天有病人来看诊时会穿连衣裙。查体需要病人掀起衣服,这块布能临时给她们遮住下半身,防止病人尴尬。
手术中,病人会突然握住他的手,韩宝三一般不会松开。“病人很紧张,这时你松开,她会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不过,结合现实来看,韩宝三认为从顶层设计和善用工具做改变,可能对推进人文关怀更有效。
以前乳腺癌多是全切手术,对病人心理和婚姻生活会产生巨大影响。
有个患者曾告诉韩宝三,得了乳腺癌之后,哪怕当时她做了保乳手术,丈夫都不敢直视她的乳房,并且从此也不再摸她的乳房。但至少对病人而言,保乳让她自己在心理上好过一些。
所以,面对早期、轻症患者,医疗上要逐步从全切手术过渡到保乳手术,从单纯保命到尽量保证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愈后生活。
工作之外,韩宝三也通过网络和公益积极科普。如果门诊病人的问题无法一一解答完,他会耐心告诉她们,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去看某篇文章,里面有详细解答。
巧合的是,采访快结束时,袁悠悠也提到,自己想用大模型做个公益软件,总结那些在医院里很难得到的答案,让病人能在医院外实时得到解答和慰藉。“那个过程确实太痛苦了,我想帮助那些得不到帮助的人。”
(文中袁悠悠、Viola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