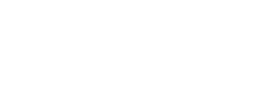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后现代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界定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这词语的提出意味着感觉与思考的某种普遍变化。它作为体验与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不再盲目地信任封闭的、进步的宏大叙事,而是以肯定的态度对待分裂、短暂与混乱。从这一角度看,新南方写作的写作姿态表露出显然的后现代解构气质,这并非西方文化思潮的亦步亦趋,而是根植于作家们对南方当代社会历史文化处境的反观内视。身处动荡的文明进程、荒谬的社会处境,面对着生活经验的长期失语,去中心、去本质的叙事技法与主题内容拓展了文学的表达边界,标识着一种认知、讲述与生存方式的新发现。这集中地体现在违反自然叙事规约的文本因素和颠覆宏大叙事的个体视角上,为我们理解新南方写作的后现代性提供了合适的切入口。
一、疾速的时代动车,生命的进退失据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指出,当代中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并非简单承袭于西方,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关系下的产物,高度表征着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复杂性。在西方与中国北方的对照下,中国南方的当代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图景,虽则文学现象不能以简单的经济政治决定论来观照,但是基本物质条件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并作为某种时代气质展现在文学中。进一步说,新南方作家的写作还直接地从文化层面表现了时代的危机与精神的困惑。
随着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南方从此作为现代化的火车头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黄金期,经济发展迅猛。北方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主要靠国有企业的支持,在新经济形态的冲击下,发展明显迟缓,弥漫着一股掉队于文明转型的荒原感。南方则深度介入时代的变革之中,全球化的浪潮、市场的争荣夺利、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这片土地永远充斥着不安分的燥热感,“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烟霞里》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时代大潮滚滚向前,泥沙俱下。20世纪80年代,主人公田庄还处于青春懵懂的少年时期,但“改革开放”的标语早已透过电视新闻、春联、收音机入脑入心,父亲田家明仕途的步步高升使时代机遇转化为家庭里直接可感的喜悦情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彻底点燃了举国上下的激情,田庄这次作为市场改革的亲历者,作为无数从县城奔赴广州追求时代机遇的人之一,亲自见证“人人都有希望”“怎么样都行”的时代的降临。那是“改开四十年中最活泼、奔放、直令人血脉贲张的最后几年青春期”,都市璀璨繁荣的景观激起物欲与虚荣心的膨胀,功利主义深刻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全民兴起创业的浪潮,“人人忙着挣钱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商圈、政界、文化界内部斗得生龙活虎、一派生机。
当“遍地是黄金”的辉煌年代不再,个人奋斗之于阶级跃升的有效性严重降低,现实残酷冰冷的一面逐渐显现,社会竞争趋向内卷,物质与精神的不协调变得尖锐,造成青年一代普遍的倦怠、迷茫困境。《撞空》的主人公何小河在广州工作,却生活得琐碎缓慢、疏离沉重,他无力追求事业上的进步,也丧失了享受幸福与爱人的能力,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流浪于城市街头。这种被韩炳哲确诊为由过量的肯定性所导致的倦怠感,互联网过度的刺激带来无限的信息,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赋予人享乐的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鼓励不设限的人生,一切看似都无穷无尽,而自恋的个体无法与这些事物建立深度的关系,“不再能够的能够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它们都变成迷乱与喧闹的幻象使人错乱。“撞空”的比喻揭示了青年个体与周围世界的“悬浮”状态,陈春成则不断在“找一处深渊供我沉溺”。不论是寄托着少年想象力的“夜晚的潜水艇”、具有通灵力量的“传彩笔”,还是隔绝人世的裁云师、神秘的酿酒师,主人公们都心无旁骛地投入私人的精神追求中,而置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于不顾。宥予漫无边际的虚无与倦怠感,陈春成对于永恒性与心灵静谧的迷恋,作为一体两面反映出在不安分的时代安顿身心的精神诉求。
南方的后现代景观与西方有迥然的不同,尽管繁华的珠三角地区已与国际接轨,经济飞速发展,充斥着迷乱疯狂的文化潮流和消费盛况,但南方内部的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非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无数人离开落后的家乡到发达都市寻找人生出路,他们大多穷困拮据,无法承担高昂的租房费用,只能居住于大城市的城中村,杂乱无序的城中村与光鲜亮丽的高楼形成了鲜明对比,形成了割裂的都市景观。《通俗小说》描绘了城中村里千奇百怪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拍电影的发廊妹、躲避城管追捕的走鬼、吃“沙县”的杀人犯、士多店的妓女、被古惑仔砍死的歌手、被暗恋的啤酒妹,他们靠着最底层的营生手段,盘踞在拥挤肮脏的城市角落。其中的《在城市之中》直接地展现了苦难与幸福严丝合缝的荒谬景观,森严的高楼、密密麻麻的广告牌、大型的购物广场、划过天空的飞机,提示着这片土地的文明、繁华与先进,而这批建筑的附近却是衰颓的烂尾楼,有人正在跳楼。都市竟可以把两个如此截然不同的世界拼贴在一起,人类的痛苦、欢笑、富裕、贫穷同时在此地发生。
光怪陆离的城市体验激发起人普遍的怀旧与乡愁情绪,它们充当都市生活的某种保护机制为城里人提供避风港的精神想象,从而实现对现实困境的短暂逃离。《潜居》里敬亭和“你”的生活被截然分割为两面,一面是世界最前沿的生意,炒比特币、操作点击量;一面是最怀旧的记忆、物件与行为方式。以符号换取符号的营生方式使人的虚幻感达到巅峰,当生意破产,他们用高科技的手段重新挖掘埋藏在水下的家乡,用玻璃罩把老房子保护起来,以荧光屏设置光线变化。“你”只有在其中才感到拥抱繁华都市的自由,敬亭则痴迷于把老房子收拾成与记忆别无二致的样子。被玻璃罩与荧光屏保护起的湖底老房子是蒙上玫瑰色记忆滤镜的家乡幻想的具象化,暴露出现实家乡与想象家乡的殊异,他们迷恋的并非真实的家乡,而是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想象的家乡。“通过未来回到过去”揭示出现代人徘徊在城乡之间的永恒“异乡人”状态,哪怕他们已获得都市生活的入场券,“无根”的漂泊感使他们无法真正地沉浸其中享受幸福,而城乡的巨大差异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回到真正的家乡的可能,这种由脱嵌产生的“进不去也回不来”的生存状态构成鲁迅“离乡-归乡-离乡”的新时代书写。
并举推进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进程将新南方作家置于全然陌生的新文明境况中,一边是文明的极速转型,人时刻处于流变与不安稳之中;另一边是庞大的、个体无力解决的社会历史问题,拖着人重重地向下坠落。作家们深感生命的撕裂感,极力书写错位的生命体验。荒诞的社会图景不仅作为基本的语境展露在文学世界内部,使新南方写作的后现代性书写呈现不一样的面貌,还作为书写的原动力,推动新南方作家寻找描述时代感觉经验的新的艺术方式。
二、同构的非自然叙事,心灵变动的艺术映照
生命世界与艺术形式具有某种同构关系,面对全新的时代经验,新南方作家除了对历史社会问题进行处境性的、故事性的思考,还须发展出一套崭新的形式话语来描述、理解更深层次的心灵结构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