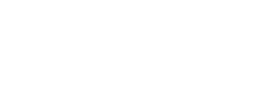李 静:林峥师姐好,很开心与你一起参加《广州文艺》的“南北对谈”。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学术训练,师姐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中山大学任教,而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比起你穿越南北的经验,我的工作生活都在北方,如此看来这确实是场“南北对谈”,很期待我们之间的“视差之见”。具体到近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南方”“新东北”“地方性”确属热门话题,对此已有诸多精彩发挥。我们的谈话,或许可以不再重复此前常见的论点,不妨把焦点放在“认识论”与“学术史”的层面,做出一些更具前提性的追问。比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南与北”或“地方性”这样一种认识装置是如何生成的?为何这类认识装置会成为“一时之选”?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南北之分由来已久,而根据方维规老师的梳理,文学史编纂中的“南北文学观”模式可以追溯至丹纳的“环境论”,并经由日本汉学家的文学史书写影响了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参见方维规《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南北文学观”的缘起与回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这样一种从“地理与文化”出发的实证主义话语模式,并非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史观与文学观。因此,如今看来南北二分的文学观念看似保守刻板,却在其起源时刻充满突破性。不知你能否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角度,为如今的南北文学观继续增添某些历史脉络?如今我们为何继续调动“南北”这样的认识装置呢,其对话对象、实际作用与突破性何在?
林 峥:谢谢李静师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曾有同行评价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北上得到学术训练,又回到南方,兼得南北,此前我还未曾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确实有趣。南北气质的不同其来有自。我记得顾炎武对于南北学者之病的评价,说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即点出南北治学风格的不同,虽然笔无藏锋,倒也切中要害。在现代文学上,“京海之争”更是奠定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格局,鲁迅那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比之顾炎武,辛辣过之。当然,“京派”与“海派”的争论,最初由沈从文发起。沈批评一班“玩票白相文学作家”“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南北的趣味分野确实存在,北京更受新文化人的青睐,比如徐志摩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屡劝她从沪来京,说:“北京实在是比上海有意思得多,你何妨来玩玩。我到此不满一月,渐觉五官美通,内心舒泰;上海只是销蚀筋骨,一无好处。”包括谈到金岳霖等友人看到陆的画,都为之有才华却在上海浪费了感到可惜:“他们总以为在上海是极糟。”而上海的文人除了作为“海派”应战的现代派以外,也包括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创造社诸人,以及后来发展成为左翼作家的群体,他们与上海为何会相互选择、双向奔赴,都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其实民国的“南方”除了上海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城市——广州。广东自近代以来屡得风气之先,是革新、革命的象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诸人都曾经为此怀着极大的憧憬奔赴广州。到了今天,“南”与“北”的界限进一步往外延展,比如“北”从民国时期的北京到了东北,“南”从上海到了两广、海南、香港、澳门甚至南洋等。我觉得也有一个从“中心”到“边缘”视角的拓展。其实北京和上海的代表意义都远大于一个城市,北京是帝都、首都,更多代表中国,上海则更多象征着全球、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超越北京、上海,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地区,是有价值的。我知道目前对于“新东北”“新南方”的概念,学界尚有争议,但我还是很肯定它作为一个认知装置,有助于我们打开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观察视界。
李 静:从你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南”与“北”的划分真是一个相对化的、从具体历史情景中产生的认知装置。顺着你的时间脉络,我还可以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再补充几句。“新南方写作”特别强调方言、民俗等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的异质性,认为其中蕴藏着突破均质僵化的写作秩序的能动力量。但若返回当代文学的创生阶段,创造带有普遍性、真理性、高度透明化的人民文艺才是终极目的,地方性与方言土语是需要被批判性地吸纳其中的。换言之,“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在新与旧、都市与乡村、现代与民间、民族与阶级等关系模式中,文化的地方性不可能获得建立自主性的理论根据”(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