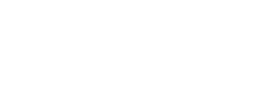忆大象
丛林间大象接近虚无
它几乎不具备形体
无限趋向一粒尘埃
但它的存在毋庸置疑
相同地,大象不再是力量的化身
投下的阴影,随时
被众多的树木抹去
大象的移动约等于静止
它的鼻息,反馈于自身
印证了暂时的在场
如此多的大象,就像
虚无叠加着虚无,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它们不再拥有
山的形象,体量和力量
在等待永恒的消逝
在它们的内心,保持着肃静
有时的狂怒,让它们找到了
更深的肃静,让它们的外形
和时间达成了平衡
忆游阴那山
阴那山的草木、乱石、山径
已经模糊。阴那山作为山名
并不抽象——蕴藏着心跳、祥光
无边的落日
阴那山一直后退
记忆中残缺的形象,像一帧照片
灰尘、水迹、霉变加深了时间
留下的刻度
这个下午,阴那山
置于记忆的中心
——灰暗、模糊
它的存在,使阴沉的窗外
不再荒凉
对于阴那山,这人只是过客
阴那山从未离开
茅洲河
茅洲河的河水来自山间
污染过,又清澈了
流逝的河水,从未间断
两岸的加工厂改成了艺术区
草木更相信自然的力量
茅洲河的鱼儿和茅草
自能辨识水流的方向
它们从不因人类的意志
而彷徨。流水中
总有一股力量
会修正盲目的轻狂
银瓶山的静
银瓶山安于东莞一隅
它的肃静
修复了这座城的缺憾
许多人赶往这里
像回到前世
叶尖上滚动的露珠
映现一张脸
真正的静,并非无人
樟树与菖蒲各自安好
像两个大小不一的漩涡
在自己的回声中
落叶回到泥土,溪流
清澈的泉水运送着
水兰草、鹿角苔、山坑螺寂寞的心
暴雨洗过的天空
蓝得透彻,之前的雷声只是警告
雀鸟的鸣叫,在枝丫间
却难以找到
石级一路向上,一如
对俗世不管不顾的出世者
他留下的足迹
让后来人徒增叹息
只有两个老冤家忽然相遇
对话间,才依稀
重回了人间
在观鸟台观鸟
白鹭在远树上
像一个虚幻的想法
无辜,但洁白无瑕
江水泛起的微波
细小,真实
有着不容辩驳的确定性
小孩子叽叽喳喳,许多人
来了,又走了
空荡荡的观鸟台,可以容下
喧嚣、哀伤和风暴
烈日下
实物投下了阴影
只有飞鸟
逝去时,什么也不留下
如 此
在飞机上,戴上眼罩
摘下时,已在千里之外
一个人,初恋时哭泣
眼泪流干了,她就
成为另一个人
在看不见的泥土里,蚯蚓
柔弱的身躯,奋力前行
它与整座森林的青翠
有必然的联系
当奔跑的力量散去,有人
获得了智慧,有人
得到坟墓
为何如此?这一切
都像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只有种子,不言不语
破壳时,就不为人知地
敞开胸中千沟万壑
荷 塘
荷塘是对房地产的警告
无声的反抗,也是低调的平衡
起初的逼迫、慌乱
一种来势凶猛的吞噬侵蚀着它们
——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他们的存在,只是姑且”
它们的块茎伸展得小心翼翼
谨慎地冒着叶尖,以免
被强大的推土机碾压
它周围那绝对的话语权
不可能听见它轻微的呻吟
只有当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响起
它们的存在,才获得确认
阳光落在荷叶、荷花的身上
暗香似乎中和了水泥的硬度
而埋藏在地下的块茎
有一把看不见的铁锹,正缓慢地
越过房地产商那高高的围墙
可乐遗址怀古
现在不一样了:喧哗、繁盛
人来人往;建设中的博物馆
打桩机沉闷的敲击声
仿佛要把繁荣钉牢
参观者们都知道,薄薄的土层底下
还埋着一个王朝,曾经的荒芜
并不能抹去酋长家宴的奢华
灯盏、酒水和死后的青铜头罩
有谁能说出,什么是永恒的?
权贵,或者山盟海誓的缔约
都随断头的血水,渗入了泥土
只有那辽阔和宁静
在树叶和露水的反光中
重复着无法辩驳的逻辑
注:赫章可乐,曾经是两千多年前兴极一时的夜郎古国的腹心地带,是夜郎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