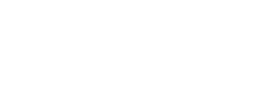朱山坡:弋舟兄,《广州文艺》开了一个“新南方论坛”专栏,已经持续两三年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奉该杂志之约我跟你聊一下“新南方写作”这个话题。我们是老朋友了,你知道我向来不善于聊这种理论性很强的东西。小说家们坐在一起也很少聊写作,最多是互相探听一下最近在写什么。大伙也不说真话,经常以“瞎忙,啥都没写”搪塞过去,但过阵子新作品便出来了。我印象中你属于这类人。其实,我理解,写作这事情跟“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道理,口袋里有银两,但不能说出来,更不能说具体数目。你最近在写什么?
弋 舟:山坡兄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当然最近也是“瞎忙,啥都没写”。“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我注意到了,不注意也不可能,《广州文艺》搞得热热闹闹,算是文坛这个阶段的“显学”了。兄喊我来聊这个话题,实在令我有些意外,毕竟,我身在西北,跟“新南方”扯不上什么关系。我想,山坡兄找我来谈,可能还是基于对我这个多年老友的信任,对此,我也就只能召之即来了,至于能不能“来之能战”,那就不好说了。我尽力吧。
朱山坡:关于“新南方写作”这个话题,聊过的评论家和作家很多了,他们都说得很好,而且说得越来越好了。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聊过,没有新的补充了。我是“很南方”的人,接触过很多“很北方”的作家和其他朋友,南北还是有差异的,哪怕在写作上,像厨师炒菜熬汤,用的配方不一样。你是江苏人士,江南基因,在西北生活多年,“南北”在你的身上应该已经融为一体,“南北”对你来说不存在明显的鸿沟了吧,就像西凤酒与洋河大曲无论是单独喝哪一款还是混搭着喝,你都不会排斥了。
弋 舟:不时制造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说法,可能也是需要的。这么多年,我们应该也适应了,至少,我部分认可文学有时需要一些“话题”的推动。“南北”之辩的确对我“干扰”已久,我现在不再觉得这是一个“困扰”了,而“干扰”也是一种温和的、中性的干扰吧。因为总还是免不了要常常被人问及,对此,我差不多是当作“寒暄”之一种了。几年前吧,《扬子江评论》搞过一次相关话题的讨论,主旨好像就叫“小说何以分南北”,他们请来了余华,然后一南一北叫了两个70后的小说家,南方是路内,北方是我,谈了半天,各说各话,余华似乎是一个裁定者的角色。现在回忆,完全想不起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是“各说各话”,但彼此之间好像共识大于分歧,部分地认同了文学的确有着南北之分野,更大部分地反对了如此简单地两分世界。至于我,诚如你言,混搭着了,不要说排斥,甚至想要排斥都没有可能,因为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南,什么是北。
朱山坡:虽然你在西北生活,但我觉得你的小说“南味”更浓一些。你声称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理解为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追求,一个作家未必要为“故乡”写作,也没有义务重点书写某个“地方”。因而,我们追求和践行的理念是一致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