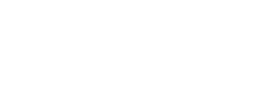若非因为农忙,或者,我现在该是一名教师。当年报考中专填志愿,母亲带我去附近的赵公元帅庙叩拜。庙里的处士代为问卦,主张报县上的师范学校,当时连打三个大胜卦,道是万无一失。母亲反复叮嘱,要按神明的意思填报,我心里却犯了难。我晓得,村里的罗良真老师,从部队转业回来进入教师队伍,家里还要作田,搞农忙。那会儿,我对农忙极度恐慌,尤其怕双抢,若读师范当老师还要作田,那考中专吃国家粮有何意义?几经权衡,我下定决心,私下改填了录取分数更高的省城商业学校。幸好,顺利考上,母亲事后几番责备,焚香烧烛祷告赔小心,而个中缘由,我一直没对人说。
在屋场,当年我家所在那个生产队因人口迁出不少,每户分配的田亩较多,农活自然也相对繁重。从七岁开始,最初是大人带到田里好玩,再到当帮工,后来做主劳,直至十七岁在城里参加工作,十来年间农忙时节我都活跃在田间地头,备尝个中艰辛。对农忙可谓深恶痛绝,如今仍心有余悸,偶尔还会梦到自己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劳作,不知何处是尽头。
那时,对于小孩来讲,农忙首先从春插开始。开春后不久,大人在田里备好种育好秧,水田放水用犁耙耕耘过后,拿楼梯横拖平好田,再纵横交错打轮子画上方格,就可以下田插禾了。第一回下田源于好奇,试过之后大人说,周缸插田有模有样,从此我就和这活计结缘。刚开始,一线过去我只能插四兜禾,大人能插七兜以上。插禾时弯腰驼背,动作简单,将禾苗用手插在方格的十字架处,要求深浅刚好,多少合适,横竖成线。人在水田里,头上太阳照耀,脚下水面反射,容易腰酸背痛,头昏眼花。插田时有人一径往前插,有人则倒退插禾。寻思过,往前插总觉得离尽头遥遥无期,偶尔回头望,看到水田一层层绿了,会有种成就感;倒退插就有不经意间到了田埂边的惊喜,相对来说禾也插得更齐整。有种特殊情况,某些地方平好田后不便打轮子画方格,大人就随手插禾,也能横竖成线。最怕有蚂蟥的水田,那玩意儿咬人吸血不知不觉不痛不痒,往往上岸洗脚时才会发现。插田时偶尔能捉到黄鳝泥鳅细鱼小虾,算作对孩童的额外奖赏。
农忙最辛苦难耐的活计是拌禾。早稻拌禾在暑期,天气酷热;晚稻在中秋时分,气温稍低。那时每到拌禾季节,天还没亮,父亲就会将我和弟弟叫醒,母亲早将下田的破旧衣服准备在床头。出门来,窗台上并排放着四把明晃晃的禾镰刀。一人拿一把到田里,天刚微亮,父亲说,趁早上天气不热,先杀五分田禾再吃早饭。四个人赤脚下田,一字排开,大人手大,一把能杀七八兜禾,我和弟弟只能一手抓五六兜。稻田里立即簌簌直响,水稻割下被摆放成一手手大小相若的“禾瓜”,排放过去,只等打谷机下田。露水深重,禾叶锋利,我们手穿袖筒,头戴草帽,很快衣服被打湿,手和脸被禾叶割出血印子。一页禾割完,到对面田埂边,又掉转头另起一页。待预定的任务完成差不多一半时,母亲会提前回家做早饭。直到太阳完全出来,光线开始发散热量,父亲才会说,回家吃饭。饭后继续杀禾,早就盘算好,就近杀完一两亩稻田,能方便利用打谷机,不必来回周转。上午杀禾,下午拌禾,露水也可尽快被晒干。
杀禾其实也有些乐子。小孩眼疾手快,能抓到土青色的蛙类,在稻田里做窝的小鸟,毛色光滑的田鼠。杀挨着田埂的那页禾最好,上面常有不知名的小花小草,或长着肥硕的丝茅根,扯下来含着满嘴生甜。手上杀禾,耳听鸟叫虫鸣不止,眼看蜻蜓蝴蝶纷飞,偶尔直起身伸个懒腰。就在这当口,大人远远杀到前面去了,见小孩在后面发愣,会大声训斥。没法,只得埋头赶上。
下午拌禾,大人将打谷机抬到田里,顺杀禾的方向摆好。打谷机木头结构,上面有铁制配件,重量不轻。我试抬过一次,和父亲一起,抬较轻的尾部。父亲让我先起肩,他再将有滚筒较重的那头抬起。刚起身,我就觉得肩膀生疼,扛受不住,想要放下。父亲未允,不由分说往前走,我在后边只得踉踉跄跄咬牙忍痛跟过去。到了地头,将打谷机放下,父亲对我说,其实也不重,霸蛮就过来了。母亲得知后,含泪埋怨了他几回。
大人将打谷机踩响,滚筒咕噜噜直转,我和弟弟负责将“禾瓜”搂起来送到大人手里,由他们在滚筒上将稻谷打下。每隔一段,需要将打谷机往前拖行以就近拌禾,大人在前面拉,小孩在后面推,田里留下长长的两道轨迹。父亲边拌禾,边要及时清理打谷机里面的稻谷,打出粗禾芒,装入竹箩筐,担到地坪里将谷晒开。拌禾时太阳正当昼,阳光直射,人们都汗流浃背,不停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谷粒打在脸上,脚被禾兜绊倒,手让禾芒刺伤,拌禾仿佛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人们用镰刀、打谷机做武器,攻占稻田这块阵地。每到日头落水,暮色垂下,大家都精疲力竭,走在田埂上脚都放软。如此,每日反复。
春插只用插田,秋收就是拌禾,暑期双抢又要拌禾又要插田,且因节气所限,拌禾插田时间紧接,中间不得停顿歇息,着实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