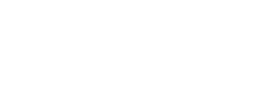时至今日,早晨醒来,意识没完全恢复,在一缕透纱而入的微薄阳光中,我会忘了睡在哪一张床上。记忆深处有两张床:一张脑袋靠墙,东西向;另一张脚靠墙,南北向。认识到那是两张年代久远的床,久到仿佛是上辈子的物件,如今的我不可能身在其中任何一张上,微微侧了下身,已然完全清醒,但愿这种朦胧状态多维持一会儿,透过半睁半闭的眼皮,努力复原两张床所在的两个房间的一切。于是以天花板的某一点为中心,依次看到房内的摆设,犹如小时候玩的显形药水,经由试管滴到一张纸,原本空白的纸页呈现各种事物的线条。
那些家具从蒙灰的幕布后挣脱出来。
在第一个房间,床尾西侧,有一个电视柜,黄漆遍体,左右四个抽屉,圆形拉环,长两米,宽一米,是旧年代的女儿嫁妆。柜子旁,一张书桌,面对南窗,窗外一丛茂盛的青皮竹,细雨中摇曳婀娜,竹旁两个露天大水缸,雨水落于缸中,泛起一粒粒小麻点,那是记忆的注脚。
第二个房间,床头柜摆着一盏幽微的台灯,柜子旁,一张电脑桌,早期的天蓝色电脑,笨重的机体发出低频率的刺刺声。再一旁,也是一件旧年代的女儿嫁妆,带镜衣橱,橱内空间宽敞,能容纳十来件衣裤、被褥,不显拥挤,镜面光可鉴人。我常站于镜前,关照青春期的唇上长出的胡髭(失眠的夜晚,总觉得有个披发女鬼站在镜中,对我长吁短叹)。
第一个房间是外婆家的卧室。
第二个房间是我父母家,即我的老屋所在地。
第一个房间消失于二十年前的拆迁,当时我正面临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大考,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重返,去完成一场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形式大于内容的告别仪式,并不认为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对于一个后知后觉且天性敏感的人,故地的意义要在很多年后才显现出来,牵扯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条目,被冠以成长路上觉行圆满的佐证:原来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不见的东西,本身会被每一朵浪花裹挟,去往那水流平缓的洼地发出光亮,日久弥香,但为时已晚,可供凭吊的只有来自旁人的讲述。
当我不可救药地日复一日思念第一个房间及它周边的一切,在霞光铺满窗口的傍晚迫不及待询问母亲,当年的拆迁是怎么进行的?母亲一头雾水反问我,什么拆迁?她是一位着眼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的主妇,过去的事件在她心中常年处于蛰伏状态,若没有激活的契机,将永远被遗忘。待弄清我的所指,她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说,哦,那个,就是好几台推土机,开进村子,把房子挖倒,别的还有什么?她也没见过,赔了一笔拆迁费,没别的,忘了。
我希望作为当事人的外婆可以为我提供更详细的讲解,可惜办不到,她落寞而孤寂地走完命定分派给她的七十个年头,被一种叫作甲状腺的病症折磨,十年如一日地咳嗽,殒命于五年前一场失败的手术。和她的房间有关的往昔与她的骨灰一块儿被葬入方夏公墓一米乘一米的正方体墓室,下葬时我出乎意料没流下一滴眼泪。
第二个房间在半年前也被纳入拆迁范畴。
消息传来,是在一个周末午后,窗外有厚厚的云层,落日坠落于远方山头连绵起伏的山脊线,光线诡异多变。父亲正在看报,差点没从沙发上蹦起来。
老屋是他三十岁(我一岁)那年建的,在家族兄弟中,他是第一个建宅基房的男人。建房前,他依靠工人家庭承袭的因素和自己的本事,进了一家国企,专事电表质量检测,那年头能坐办公室是了不得的事,他的兄弟,不是学了木匠,就是入了水族业,靠劳力吃饭。那是他的黄金时代,是一生中屈指可数的高光时刻,在我记忆中,他每天穿着天蓝色工作服,骑上凤凰牌自行车,风光体面去上班,下班时,给我买一些玩具,惹得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年就赶上国企改革,国转私,企业大面积裁人,他不幸位列其中,失业了,于是从头再来,找了一堆工作,无一技之长,最终在时代罅隙中,活成了一个笑话,辛苦自不必说,收入少了一大截。后来城市化建设推进,兄弟亲朋陆续搬离氏族同居之地,入住商品房,他由于家道中落,怎么想方设法,吃苦耐劳,没能力赚出一套小高层的钱,落后于曾让他瞧不起的弟兄们,将罪责归咎于老屋,是老屋的存在压缩了他施展本领的空间,如若没有老屋,他也能住进商品房,对老屋横竖看不惯。尤其是2007年那场台风,大雨填平河道,大风吹倒树木,地势较低的老屋被河水、井水、阴沟水混合而成的那么一种奇怪水质灌入,浸泡了三天三夜。他面向西天,痛定思痛,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腾笼换鸟,倾其所有,终于在距离老屋两公里的青林嘉园小区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商品房。
他将老屋划分区域,分租给六户拖家带口的外来打工者,笑称自己也是有房出租的包租公了。我们这儿租房有两种方式,一是将房子囫囵承包给二房东,由他找客源,房东只从二房东手中抽取固定租金,做个托盘掌柜,事虽不管,到手的租金比较少,我二伯就是这么干的。父亲不愿意让二房东盘剥一道,决定自己动手,客源自己找,租房期间的所有事也一肩挑。自租房那天起,老屋仿佛故意和他过不去,频频出差错,下水道堵了、电表坏了、墙角漏水了、水管爆了……租户们来找他,他都给解决,会的自己上手,不会的请人修,搞得他焦头烂额。揽着那些租金,心事重重,对老屋的怨恨越积越多,每听到哪个区域拆迁了,总会露出羡慕的神情,期待拆迁——成了他一桩沉重的心事。
我在老屋住到二十五岁,二十五岁之前,一栋房子对于我的意义除了束缚自由,别无其他。叛逆期维系得比别人久一些,横跨整个学生时代,邻居小孩能在书桌前坐足两小时,捧着书本温习作业,我一刻也待不住,一心想往外跑,最好夜不归宿。我把头发养得很长,偷偷抽烟,口吐脏话,学弹吉他、高唱摇滚的热情比掌握数理化内部的逻辑更为强烈,父母一度以为我会变成坏孩子,跟着地痞混大街,寻衅滋事,目露亡命徒的凶光,在一场人数众多的斗殴中被人弄瞎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