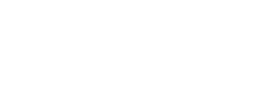大 雪
那些日子像一场大雪,朦胧而虚幻,不甚真实。但真的是虚构的吗?
我记得那个冬天,路过小河村时,脚下一滑摔倒在雪地里。我躺着,不动弹,感受雪那种冰凉的寒意穿透羽绒服的厚度。麻奶奶拉起我,说着:“快点呀,蔓蔓一只脚踏进阴间了。”
雪停了。雪地上,拓下一个年轻女人身体的痕迹。如果把这个印痕当作模具,会不会脱模出另一个自己?我不知道。
细瘦的一条河,已经封冻,河面上厚厚一层冰,又覆盖厚厚一层雪。我听见咔嚓一声,麻奶奶栽倒在雪里。她躺在雪地里,不动弹,我以为摔晕了。
村子里都是白土夯筑的矮墙,墙头枯黄的芨芨草,俯仰,摇摆。墙上刷着白灰标语,有一个字是错的。但是白土墙不管这个。冬天的白杨树枯瘦干巴,像年老衰败的牲口,只剩下一口气,一身乱毛。
蔓蔓也只剩下一口气,汗水黏着头发贴脸上。她躺在土炕上,身下垫着的被单被血浸透。看见我,深陷进去的眼珠子,涣散无光的眼珠子,带着点微黄的眼珠子,回光返照那样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婴儿卡在产道,能看见粉红的头皮,稀疏地粘在头皮上的发丝。
连羽绒服都来不及脱掉。我跪在蔓蔓身边,伸出剪刀咔嚓一声侧切。然后长钳子夹住婴儿脑袋,对蔓蔓说:“别怕,深呼吸,用力。”
蔓蔓用残余的力气最后吼了一声。这一声吼出来,婴儿包裹着白脂,像一嘟噜葡萄那样扑通滑出来,掉在浸透血的布单上。他举起小拳头,挥舞着,想捣我一拳。是我把他接到地球,先打个招呼。
婴儿挣扎着想哭,没出声。我伸进去手指,掏掉他嘴里的胎膜。哇一声大哭,炸开在屋子里。小脸儿皱皱巴巴,看上去像九十岁。
蔓蔓也在哭。没有声音,眼泪糊满脸。湿头发糊满脸。
“没事,蔓蔓,娃很好。”我额头的汗水顺着脸颊流到脖子里,嗓子干到冒烟。
“是个啥?”她的声音似乎是从地缝里挤出来的,颤颤巍巍。
我扒拉了一下婴儿,是个男娃。蔓蔓脸上立刻松弛下来,眼珠子有了光。她动了一下,伴随着微弱的呻吟声。
脐带缠绕在婴儿脖子里,小脸儿挣巴得紫红。他紧闭的眼睛微微睁开,打量着这个世界,伴随一声一声啼哭。
好险啊,差一点你就不能降落地球。我舒了一口气,对他笑笑,尕蛋蛋,不错哟!
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听到的第一个人类的声音,柔和,细长。说话的女子拨开他脖子里缠绕的脐带,手套上沾满滑溜溜的液体,握着手术剪。
小婴儿一伸手,扯住我的袖口。他牢牢攥紧我,像重逢,像梦境,又像爱而不舍。那只小小的手,粉红,糊了胎脂,一枚树叶似的。
咔嚓再一剪子。脐带的血溅出来,溅到我白色的羽绒服上。嘶嘶倒吸了口气,刚买的新衣服,准备穿个三五年。
“脐带剪得太短了。”麻奶奶不知道啥时候驼背弓腰站在一边,含糊嘟囔。我以为她一跤摔晕过去,结果没有,连滚带爬赶来了。
“阿奶,脐带不能太长,会感染。”我回了一句。半小时之前跟她说了,我是学中医的,不接生。但是她不管那个,蔓蔓快不行了。她狼撵着兔子一样把我撵来,一路狂催,恨不能一脚把我踢到蔓蔓跟前。
我晕血。实习的时候,好几次被人扶出手术室。有那么一次,孕妇大出血,我看了一眼,天旋地转,靠着墙根溜下去。
麻奶奶散乱的灰白头发遮住脸,那一跤摔得够呛,真的差点摔死。婴儿哭得不够响亮,我给了一巴掌——你来到地球,就得挨打。
挨了打的婴儿包裹在小被子里,皱巴巴的小脸糊满白脂,哭着挣扎出一只胳膊,凌空乱舞。我把他抱到蔓蔓脸颊,那只小手摸到了妈妈的脸,摸到了脸上的汗水和泪水。哭声减弱。
“这是你的娘亲,现在你已经离开了她的宫殿,独自生长。妈妈很爱你。”我笑着说。我从不怀疑婴儿听不懂。这是他来到地球之后,听到人类的第一声叮嘱。
麻奶奶一再絮絮叨叨,不要输液,家里没钱。烦死了,这个吝啬的老太婆,恨不能一脚踹走她。
“现在必须止血,不然蔓蔓有生命危险。”我没理睬老阿奶,一针扎进蔓蔓的血管里,清凉的液体顺着透明细管流进蔓蔓身体。又把几粒药片,塞进蔓蔓的嘴里,灌给她一口水。
蔓蔓哽咽了一下,咽下去,看我一眼。后来她说:“那一刻,我看你就跟菩萨一样,头顶有光芒。”
一切都在过去,包括时间、呻吟、汗水泪水、婴儿的哭啼。蔓蔓睡着了,婴儿睡着了,世界平稳运转,潜伏着强大的生命力。
清洗过的器械搁在白色的方形盘子里,酒精燃烧出蓝色的火焰。药箱敞开着,白布消毒包,绷带,两瓶葡萄糖,几盒针剂。
麻奶奶往炉子里加了烟煤块,暗红色的火焰蹿出来,屋子里一下子温暖。蔓蔓又呻吟了一声,脸色黄黄的,像一根秋天的草,倒伏在炕上。
我出门的时候,小婴儿半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后来我仔细回想那一眼,似乎满含着心有灵犀的那种熟稔。那孩子后来长成个小胖墩,每次看我,都是那种深沉默契的眼神,不像一个小孩的目光。也许在生命轮回里,我们有过相遇,只不过今生又见。
门外寒风卷着雪呼啸,卷着一个年轻女子涉过结冰的小河,走到大路上。衣襟上的血迹已经结痂,红红的,像感叹号,感叹生命不易。在天空大地之间,大雪填充了所有的空隙。
消失的羊群
一所破旧的蓝砖瓦房。火炉,碗柜,几双穿旧的鞋子。木头盆里泡着衣服。青砖地,扫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弥散着一种味道,说不清,是不洁净的那种。
卜丫丫斜躺在木头床上,盖了半旧的印花被子,脸色晦暗,一看就是气血不足的劳虚。
两个小孩在院子里打架,每人都挨了巴掌,伴随着一个粗鲁男人的呵斥声。卜丫丫不停地生病,令他感到绝望。他不得不洗衣服,把小孩子穿破的鞋子拿去修补,煮一锅羊杂可以吃三天。
我把液体扎进卜丫丫的血管,然后等待,一瓶输完换上另一瓶。我的诊所里有输液室,但是卜丫丫软晃晃的腿子走不动路。如果被架子车拉到诊所,未免又显得病入膏肓,她不想那样。
漫长的等待很令人烦闷,尤其是屋子里不洁的气味。卜丫丫在沉闷的时间里,慢声细语讲述她生病的缘由。
病是累出来的——小产没几天,娘家两群羊丢了,立刻赶回去跋山涉水找羊。找了半个月,羊毛也没找到。那些消失的羊,留给卜丫丫一身病,流血,身子瘫软,拖不动腿,疲软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