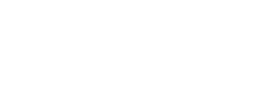仁增夏让在自家的门口坐了一下午。
忙了一辈子的仁增夏让,为什么选择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什么也不做地把自己空放在门口一下午,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只是那天下午的仁增夏让,突然什么也不想做了,他的前脚跨出门槛,后脚拖在身体后面不想往外走。他下意识地往后脚上使了一把劲儿,那一把劲儿不大也不小,让仁增夏让想起自己在拔地里的一个元根萝卜,或一株玉米苗使出的那一把劲儿,不过劲儿是相同的劲儿,用的对象却完全不一样,一把劲儿是使向庄稼的,一把劲儿是使向自己的。拖在仁增夏让身后的那只脚在他的使劲中,一动不动,跟本身就生长在那里一样。仁增夏让无奈,他想自己活到这把岁数了,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最大的能耐就是管理好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庄稼,却不能像管理庄稼一样,管理好一条亲近自己的脚。仁增夏让还想像拔元根萝卜或拔玉米苗那样,再拔一次那只不想走出门的脚,手伸过去了,劲儿铆足了,他却放弃了。不想出门就不想出门,又影响不了什么,自己一天不下地干活和自己天天下地干活,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不也没多大区别吗?这样一想,他把跨出门槛的那只脚收了回来。那只脚倒是很听话,还没等仁增夏让太多反应,脚就很快地把自己收了回来。那只脚收回来,仁增夏让的整个身体就全部在屋中了。
仁增夏让就是在自己身体完全回到屋中之后,突然就什么都不想做了。他把前年才从索南铁匠那里打的锄头一个顺手扔到院坝里,把背在背上的花篮子背篓,取下来一个顺手扔在院坝里,丢掉这些东西,他觉得身子轻松了很多。他站在原地,看被自己扔出去的花篮子背篓,在院坝中间一圈两圈地滚,花篮子背篓不滚了,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把自己陷在了门槛中。之所以说陷,是门槛中间有一个被仁增夏让这些年走出来的凹槽,他一把自己坐下去,这些年被他走出来的凹槽就在屁股下面等他,仿佛这些年凹槽慢慢在门槛中间长大自己,就是在等有一天像这样的一个仁增夏让软在自己的怀抱中。仁增夏让身体里仿佛有某样东西垮塌着,他能听见那正在垮塌的声音,隐隐响在自己的胸膛里、舌尖上、骨心中。仁增夏让没有办法阻止它,除了等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再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
仁增夏让陷在门槛中间,手心痒痒的,空下来的脊背一阵一阵地凉。他知道那是自己的身体在和自己说话,手心不习惯忙了一辈子的仁增夏让,突然一个下午不用自己,背不习惯背了一辈子背篓的仁增夏让,一个下午就那么把自己闲在那里,它们都早早养成了随时随地帮仁增夏让的忙,它们早早成了仁增夏让日常生活中忙的一部分。
仁增夏让揉揉发痒的手心,用软手敲了敲一阵一阵发凉的脊背,嘴里嘀咕着:“歇息一下,我们该歇息一下了。”他说完这句话,手心接着痒了一会儿,然后不痒了;后背接着发凉了一阵,也随着他随后的敲打不发凉了。这么多年,它们都听仁增夏让的话,它们只是不习惯忙了一辈子的仁增夏让,突然有一天就把自己空空地放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它们跟着仁增夏让忙了一辈子,有一天不忙了,总觉得怪怪的。这种感觉像一匹奔跑了很多地方的马,一直在奔跑,虽然很劳累,但奔跑已经成为一种惯性。还好的是,仁增夏让告诉它们该歇息一下了的话,是他对它们停不下来惯性的一种安抚,它们听仁增夏让的话,慢慢把自己调整到停下来的状态。
仁增夏让用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膛,胸膛里发出空空的回响,仿佛他敲的不是自己的胸膛,而是一面很久没有用过的牛皮鼓。仁增夏让知道有些东西来掏空自己了。他定了定自己,安慰自己,不必太伤心,该来的总归会来。他想到去年离开凹村的诺布,诺布走的时候来找他喝酒,喝着喝着就让仁增夏让敲他的胸口,敲他的头,仁增夏让不愿敲,诺布把仁增夏让的手一把拉过去,红着脸说:“你敲,叫你敲你就敲,别像个女人一样拖拖拉拉的。”仁增夏让缩回自己的手,对诺布说:“有什么可以敲的,你诺布有的我都有。”诺布鼻子里呼噜呼噜喘着粗气,像头即将发怒的野牦牛:“仁增夏让有些话别说早了,你敲敲就知道了。来,你敲敲。”诺布又把仁增夏让的手拉过去,喝酒醉的诺布,手跟铁一样坚硬。仁增夏让想,敲就敲,没什么大不了的。仁增夏让先用手敲诺布的胸膛,就那么一下,他就惊到了自己,诺布的胸膛发出空空的回响,他又敲了一下,那回响声更大了,好像来自一个遥远、深邃的地方。仁增夏让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诺布,满脸皱纹的诺布,此时脸上堆着傲气的笑,那被笑容充溢起来的条条皱纹,显得饱满而又鲜活。“敲这里。”说着诺布把头伸向仁增夏让,满脸的笑面向脚下的地。仁增夏让听见诺布在笑,吱吱的,老鼠一般。仁增夏让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过去,敲了一下诺布的头。这一敲,仁增夏让发现诺布的头敲出的声音,和刚才他胸膛发出的声音一样,空空的。他想自己一定是喝醉了,他不相信一个活得好好的诺布,怎么敲到哪里,哪里都是空空的;他更不相信现在正在和自己又说又笑喝酒的诺布,已经是一个空空的诺布了。
“这是我的秘密。”诺布抬起头,看着仁增夏让不可思议的眼神,得意地笑着。
“起初我也不信,但后来越来越信了,牛犟的,原来人是可以把自己活得没有自己的。年初,我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空,好像有样东西每天在体内掏空自己。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麻酥酥的,那感觉说来就来,像几只蚂蚁在自己的体内爬。特别是月亮大的夜,那种麻酥酥的感觉更加浓,似乎亮白的月光也在索取我身体里的一些东西,很多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远离我,不想要我。不过说来奇怪,我一点都不悲伤,反而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快乐了。”诺布说完这话,没等仁增夏让回应他,举起银碗就把一碗青稞酒咕噜咕噜倒进了嘴里。灯光下,仁增夏让看见酒从诺布的喉咙里急急地流下去,让仁增夏让觉得眼前的整个诺布像一块荒地,那碗青稞酒就是浇进诺布身体的一汪清泉。清泉一淌进一块叫诺布的荒地,一下就被诺布干枯的身体吸收了。那晚仁增夏让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他只想把自己醉倒在酒里,和酒一起入睡。
诺布走时,没有告诉仁增夏让第二天他准备做什么,人在喝醉酒的时候,谁都不会把第二天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