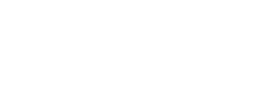贾尼玛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但他每次总会这么自我介绍:“你好,我是贾尼玛。你可以叫我尼玛,在藏语里是一个神圣的词汇,指光明的意思。不过我不是真的尼玛,而是‘假(贾)’尼玛!哈哈哈哈!”在他自觉讲了一个很棒的谐音梗、得意仰头大笑的时候,旁人总是一脸尴尬,附和也不对,不附和也不对。这样时间久了,大家也就忘了他本名叫什么。
认识贾尼玛是在S大学的一场讲座上。那次我去分享新书《天海小卷》——延续《山海经》神话脉络的奇幻长篇,主人公游历海底鲛族、天宫羽族等奇诡异域,通过吟唱的形式传送精神性力量。其实是一本探讨艺术价值的寓言之作,但出版社为了销售,把封面做得跟二流言情小说一样,让我每次都羞于展示。
会场偌大的阶梯教室密密麻麻坐了满堂,多数是本校学生,为等活动结束的打卡任务。在一水儿的年轻面孔中,有个穿着紧身裤、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格外扎眼,他堪称最为认真的听众,对穿插的每一个笑点都热烈鼓掌,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线,整张脸好比椭圆的大鸡蛋上裂开缝,但因过于卖力反而略显迥异。在最后的问答环节,此人抢先高高举手,拿过话筒说了一长串自我介绍,便是以上面那段话开头,其后紧接着长达数分钟的植入硬广:
“我最近在筹办一个艺术驻留项目,以海边文娱小镇为出发点,调研本土文化并发展当地特色。跟中心城区高密度疯长的城中村不同,那是一个不急不躁、慢条斯理的非典型村落,以客家文化为主,建筑保持着一二层楼高,各式各样的民宅和小菜田散落在街道之间……”
“等等,这跟今天的讲座有什么关系?”主持活动的院长忍不住叫停这段滔滔不绝,“这位先生,你能简短地讲完你的问题吗?”
“好,好的。”贾尼玛急得有点结巴,语速也快起来,“所以这个项目将以此为出发点探求不同人背后与这座特殊村落之间的独特关系……”
院长忍不住再次强调:“问题?问题!”
贾尼玛只得中途刹车改口:“我的问题是,你小说里写的鲛人故事有没有考察过真实原型?”
探究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算一个常见的问题。我清了清嗓子:“小说毕竟是基于真实之上的改编,更何况鲛人传说来源于难以印证的远古神话。为此我曾遍查史料典籍,《山海经》《搜神记》《博物志》《岭海异闻》等古书都有记载,小说设定则对此进一步扩展、丰满。至于你说现实里有没有真实原型,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即便最有学识的博物考古学家目前也难下定论。”
题材涉猎历史与现实间的夹缝,自然会遇到这类追问,所以一套完整话术是在图书出版前就想好了的。我以为答得周全,岂料贾尼玛抢回话筒还要接话:“这样不对,你作为作者不能只看书上的资料……”
院长摇了摇头,工作人员见状去收他的话筒。我一时嘴快跟了一句:“那要怎样?”
在全场侧目之下、话筒被收走之前,贾尼玛坚持掷地有声地抛出最后一句:“要来参加我们的国际艺术驻留项目……”
除了这个小插曲,分享会还算顺利。会后的晚宴上,院长掏出他私藏的白酒跟众人分享,我虽不善饮酒,但也抿了两口。冒着热气的椰子鸡火锅端上来,烟雾缭绕中,院长几杯下肚喝开了,提起今天的事又高谈阔论起来:“你加他的微信了吗?千万别理!这种人我见多了,每堂课上都要凑过来几个,找我们的老师去参加活动,其实什么待遇都给不了。毕竟在S市,想靠空手套白狼分一杯羹的实在太多。迟早要叫学校管管,让保安一个两个都拦在门口!”
“是啊,够奇怪的。”我扯起嘴角赔着假笑,打哈哈应和了两句,心中不免犯起嘀咕:当时他夹在一群涌上来的观众中,好像是扫上二维码加好友了?
等深夜回到酒店,果然贾尼玛已从微信上发来活动公函。想到院长的话,我仔细查看那份项目细则,不出所料当中没有提到任何报酬事宜,只说创作费由所有艺术家分配共享——哼,作为文字为生的写作者很明显拿不到什么。关掉页面之后,我顺手查了查那古村落的名字,有点熟悉,一时记不起在哪部典籍见过。过了半小时,洗漱上床后忍不住又打开文件:
“项目公开招募五名艺术家,包括编导、表演、音乐、写作、视觉艺术、跨媒体交互类等媒介,协同达成整体创作目标。”在作者圈子里待得久了,知识分子的脾气秉性都太熟悉,一个眼神就能猜到半真不假的心思,也甚是无趣。借此机会去瞅瞅其他行业的人如何交道,这位“假”尼玛又将怎样空手套白狼,也不失为一场体验。
毕竟,虽然没有报酬,但食宿全包的。
到达渔村是在深夜,灯光昏暗的街道上,一间间海鲜餐馆、酒店民宿、杂货商铺并列而置,除了浓烈的鱼腥味和稍矮的楼层,似乎与市里也没什么两样。“这还是外围,往里走。”贾尼玛在前面招呼,我跟他穿过摆满大排档餐桌的广场,踏进一道铁门,来到传说中的文娱小镇。
“为什么在村门口设一道栅栏?”还是要把我们关起来?我其实是这么想的,又觉得这个念头像被害妄想症,没有说出口。
“这要回头问问村里人。”贾尼玛帮我提过箱子,带路往里面走去。天色已黑,建筑也看不清楚,四周没有农田,反倒矗立着几间网红咖啡厅,屋外爬满树藤,摸了摸都是塑料假草。
七弯八绕走了几圈,终于在某一栋小楼前停下,贾尼玛把钥匙交给我:“就在二楼。”离去之前丢下最后一句:“以后你可以叫我老贾。”
屋内已经换上洁白的被褥床单,宽敞的两居室,一面大的落地铜镜和圆形餐桌,俨然经营成熟的民宿模样,仔细查看枕套上却有一丝可疑的血迹,不知是蚊子留下的,还是前一任房客。我喝了口水,顺手把水杯放在窗台,打开行李箱,撸起袖子换上自己带来的三件套。
被角刚套到一半,却见窗台边的杯子在微微倾斜,我扶了扶略感眩晕的脑袋,身体也在打晃。怎么回事?难道来小镇的第一天就遇上台风季?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像成百上千的蚊子列队嗡嗡过境一般,以稳定持续的低频传来,在耳边循环穿梭、游走,眼前竟闪过绿色光芒的幻觉。我翻遍了整个屋子,没有找到声音的来源,也忘记了时间的流动。再过一会儿,这声音又变成磁盘卡带那样断断续续,再逐渐加强,好像高铁嗖地起飞了,最后只听咣当一声巨响,杯子摔落在地,声音也即刻停住——我吓得一激灵,瘫坐床上。
后来声音再没出现,仿佛只是一场幻觉。但这份诡异让我整晚都瑟缩在被子里,甚至不敢出门,第二天的早饭也草草啃了几口面包解决,直到主办方召开驻留工作例会,才不得不踏出门。
会议设在网红咖啡厅的二楼。白天才看清,墙体刷得洁白,上面用稚嫩的笔触画出几条肚子肥硕的蓝色海鱼和水草,门口则摆着一只两人高的、胖胖的卡通鱼形塑像,楼梯的过道粉刷成鲜艳橘黄色,配上午后刺眼的阳光,竟让人梦回墨西哥——怎么说呢,放在这样的渔村里,就像耕地农民穿上了普拉达的毛背心。
首次见面,会议室里六七个人围坐长桌,有的埋头看电脑,有的皱眉刷手机,有人戴着墨镜好像睡着了,还有个外国人躲在角落独自啃饼干,空气中弥漫着无声的尴尬。这种时候,就是比耐性了。很明显在座各位都是真正的艺术家:社交技能偏低,而耐性十足。
终于贾尼玛忍不下去,开始逐个点名,于是一位梨形脸状的长发女孩第一个开口,发言前还极有仪式感地举了举手:“大家好,我叫子陌,目前在做独立编舞,曾获得英国和中国香港音乐舞蹈学院的双学位。我来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对渔村很感兴趣,也想跟不同领域的艺术家碰撞火花。”说完她左右望望大家,略显做作地笑起来,两颊泛起惹人注目的梨涡。她跟我中学时候的闺密同名,模样也让我想起念书时最受班上男生喜欢的那种女孩。看来怪异的性格各有各的怪异,而甜美的大都相似。
气氛热了一丝,其他四人先后发言。外国人卡顿是个英国老绅士,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头发鬓角都发白了,但人很精神。播放PPT给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就花了一个多小时,是那种结合了动力学、光学、机械工程、交互运用等综合性的装置艺术。比如在自行车前装上一个骑踏发电的空气净化器,相当于给自己在雾霾漫天中开辟一处新鲜空气的区域,令人惊叹的奇思妙想,据说媒体称他为“Ironman(钢铁人)”。另一个男生叫阑丰,瘦高个,做的是近现代思想史,话很少,只简单介绍自己研究“集体潜意识”。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了解那是荣格心理学的一部分,但在他的表述里好像又不一样。还有个戴墨镜的女生涂了烈焰红唇,全场都在打瞌睡,要靠不断抽烟来保持清醒。她叫安,是声音艺术家,搞的是电子音乐,“很震撼,整个穿透身体的力量,听过之后我几天都出不来。”贾尼玛夸赞道。这描述让我莫名想起昨晚的震颤声。
“所以你们这次驻地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自我介绍完毕之后,贾尼玛开始引入下一环节。
我曾读过许多鲛人的文献,又在书中写到奇幻故事,如今来了海边,自然想要近距离触摸海洋、渔民和渔村的呼吸,搜寻鲛人传说在现实中的遗迹——虽然那是传说,但在各文化体的神话里都有出现,应该不只是巧合?我说完扫了眼桌上的几人,安打个哈欠,阑丰在看手机,子陌盯着她面前的桌子似乎没有听懂我说的话,而卡顿百无聊赖地望向窗外,压根就听不懂中文。
我来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跟不同艺术家交换经验——但现在看来并不容易——暗叹一口气,这句俗套的话终究没有出口。
没等下一个人发言,会议室的门就被推开,突然从外涌进来一群中年男人。贾尼玛几乎是跳了起来,眼睛再度眯成两条皱巴巴的线:“哎呀,领导来了!”
他一一介绍,来的分别是街道办负责人、旅游公司老板、项目制作人等,然后就是漫长的领导发言:“我虽然是外地人,但真的很喜欢这个村子,可以给我一份安静的心,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我对这次驻留计划没有任何要求,就是希望你们跟我一样爱上这里!”旅游公司老板是个圆头秃顶的中年男人,摆出的格局姿态果然高,听完这话,我几乎想在心里鼓起掌来。
贾尼玛就跟我不一样,他不把赞美藏在心底,而是激动地抒发出来:“我觉得林总说得太好了!这个村子确实很美,而且各位的热情接待更让我们心中温暖……”他的抒情比老板说的时间还久,为此会议战线再被拉长,直到饭点才结束。
临走前,贾尼玛透了句奇怪的话:“之所以发出邀请,是因为这里其实跟你们以往的创作相关。希望通过你们的观察来发现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