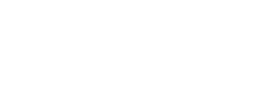熊建林把烫手的年糕饼摁进白糖瓷缸,还没送到嘴边,就开始吸溜热气。糖粒和焦脆的饼皮在口中嚼得嘎嘣响,像是点了一嘴爆竹。
这是于家媳妇的拿手菜,每当她端出一盘圆圆整整的年糕饼时,熊建林就忍不住赞美她的厨艺,说:“嫂子,当初怎么就没人把咱俩说合说合?”又装腔说:“还是我没口福啊。”
于家媳妇听到便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烙的饼你一顿也没少吃。”
熊建林像得了便宜似的,说:“骂人也好听。”又啧啧地感慨:“你瞅老于,戗毛扎沙的,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白瞎了你这个人。”
老于的笑声从菜地里传出来,他也不生气,说:“不白瞎。我家这老些矿。”熊建林呛了口吐沫:“犊子,还有矿?”老于头发稀疏的脑袋从茂密的黄瓜架子里钻出来,隔着宽阔的院子,对熊建林身后的房屋指指点点,然后说:“三个门框,好几个窗户框。”
熊建林连笑带骂,饼渣喷一地。
老于从菜园走出来,臂弯里一筐顶花带刺的黄瓜,手上一杈暖粉色的海棠果。他关上菜园的篱笆小门,把门口的黑公鸡驱走,又丢给它一片新鲜的白菜叶。
熊建林接过海棠果深吸一口气,果子馥郁的芬芳混合着山林中各种香气把五脏六腑洗得干净透亮。
老于说:“你嫂子,远处不说,咱乡里肯定算乡花了吧。”
“那肯定,我嫂子个儿最高,我嫂子脖子最长,鹅都没她脖子长。”
“搁以前肯定送进宫去了,哪还有我的事。”
“你得感谢你祖宗十八代。”
于家媳妇笑得直不起腰,转身又去给他们煮了盆锅茶。
桌子摆在白杨树下,十七棵白杨也是于家院子的边长。坎子下一条山涧轻轻环抱院子,又向下跑去消失在密林之中。老于用山泉水拦了两个鱼塘,养了百十条鲜艳的火鲤,大大小小,连成片地出现在绿水青山间,那美丽的红色总会让人感到喜悦。山风带着泉水的清凉,把杨树叶子吹得比风铃还好听。
熊建林茶足饭饱,兜里装上海棠果,往山上去。经过一条窄道,于家夫妇随意撒下的花籽,雏菊,胡枝子,一丈红,婆婆纳,如今繁花稠叠,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日照下异常明艳。远处的向日葵在悄悄转头,脚下的鸡冠子在舒展花穗。巡山对他来说早已不是责任,而是福气。
身后有车辆驶来,在熊建林身边摇下车窗,说:“请问,这是黑山吗?”
“是。”
车窗关上前后座的人说:“真的哎,也不黑啊。”
熊建林抬眼望去,清朗的天空下全是绿色。闭上眼,会觉得气味都是绿色的,一种湿润的盎然的绿。室内待久的人会觉得这绿是令人吃惊甚至眩晕的。
所以熊建林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作黑山,他出生在这里,但也从来没听人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来由。他小的时候觉得县里其他地名更好听,鱼儿山、海留图、元宝五峰白云洞。黑山嘛,美感上差了点,也不够形象。
后来他长大些,去城里工地上搬水泥,那几年他几乎忘掉了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他回乡奔丧,到家时已入夜。大火后黑山的影子在幽蓝的天空下显得萧瑟悲凉,可身边的焦土上已长出嫩芽。熊建林从中看到了一些可贵的东西,黑山这个名字在那一刻变得十分妥帖、巍峨、简洁且可靠。为了表达对黑山的感情,熊建林当时就为以后的孩子起好了名字,无论男女,就叫熊黑子,意为黑山之子。
黑子后来对父亲起的名字很有些意见,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熊建林原本要按计划巡山,走到山顶,在涌泉寺的断碑前歇脚,再从另一侧下山,折回到于家院子,一来一回半晌时间。可当他瞥见那辆皮卡车厢里拉载的物品时,不得不改了主意,随着车辆翻起的尘土,也跟着往山谷里走去。
盘山路会绕一个大圈,熊建林眼看车辆越走越远,便抄近道,拽着柴火爬上山包,循着枝头的红丝带,找到一条隐约在山林间的岩径。他的到来打扰了拥挤生长的草木,还有枝头啃手的小松鼠。
翻过山包,来到开阔的芳草地,刚才那两辆车已经搭好帐篷,正预备点火。熊建林上前搭话。几个人眼神躲闪,埋头干活,只有刚才问路的年轻人来迎。这帮肯定是外地人,他们有种新毛病叫社交恐惧症。熊建林头一回听新鲜得不行,全县十五个乡十一个镇,从来没听说过谁看见人不知道怎么说话。这里的人,熊建林常想,是怎么在不见面的一个小时之内又经历了一个小时也讲不完的故事的。
来迎的年轻人圆脸盘子粗眉大眼,有几分像熊黑子,长得挺合熊建林心意。
“玩归玩,不能点明火哈。”
年轻人的笑脸僵了一下,问:“您是?”
熊建林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红袖章,顺带掉出几颗海棠果。红袖章套在左臂上,熊建林矫正了字的朝向:防火巡查员。
“吃点冷的,不用烧的。要不山下有个农家院子,就你们刚路过那儿。庄稼人做饭没什么场面菜,但旁处也吃不到这味道。”
年轻人捡起地上的海棠果,往身后看了一眼。一把露营椅上一个中年人在兴高采烈地指挥他面前的七手八脚:“肉待会儿再拿出来……拆开炭包……点有凹槽的那面。”熊建林欲上前阻止,年轻人拦住,略一迟疑,说:“大叔,你这海棠果闻着香。我买几颗。”
“拿着吃吧,我兜还有。”说着,熊建林上下拍兜,把海棠果翻出来,递过去时,遇到年轻人手里的钞票,扇形状打开,五张。熊建林纳闷,城里人都什么消费水平,满山的野果已经说了不要钱。
年轻人说:“您行个好。我保证把火灭掉。”
这年轻人三十岁左右,皮肤不算白皙,但肯定不是干体力活的。他留的是利落的寸头,穿一件粗布天蓝色的衬衫,肩膀厚实宽阔,给人一种很敦厚的感觉,但此时他脸上却是卑怯的表情。熊建林这才明白年轻人不是要买海棠果,而是要买通他。
熊建林有点不忍心又有点恨铁不成钢,他说:“谁保证也不好使,有的是前车之鉴。要不定下这规矩呢,林子里点火是天大的事。”
熊建林嚼了两棵野韭菜,年轻人还没有走到他领导面前,不过已经制止了要点火的人。于是熊建林也不着急,他弯腰采了一把韭菜花,又单拿出两根绕着花梗缠几圈,捆成一束有浓烈辛辣香味的花束。
年轻人的领导嚷出了声,像是被浇了桶冷水,要恼。年轻人低头说了几句什么,把领导往车上护送,又扭过头忙里偷闲地责令众人迅速装车。
熊建林看着那两辆车往山谷深处开去,他不放心,但又跑不过车子。他站在原处,让腿和理智做了一会儿斗争。云影从他身上飘过,太阳照得眼皮酸唧唧的,他眯起眼睛往山上看。忽地,山上草木翻涌,痕迹弯弯曲曲时断时续,像是风有了形状,又像一个庞然大物隐了身。熊建林心生一计,打个电话骗老于快来,叮嘱他一定要骑上摩托,麻溜的。
熊建林从小就知道林子大有神秘。脚下的草地,雨水丰沛时是条小溪。听说有一天巨蟒下山喝水,头已扎在溪水里,身子还在山上。有山民路过,巨蟒转头,带来雄浑的气流将山民扑倒。山民仰面倒爬,逃回山下。据说,一条蛇眼有一头牛那么大。
传言后来变得细节翔实,情绪饱满。作为传言集散地的于家院子,却从未能传出那山民姓甚名谁。老于的爷爷于老爷子还带人往深山处探寻过几次,什么也没找到。大家合计,在找的是已得道的仙子,自然无迹可寻。后来修路、开矿的工程,惮于仙子的盛名,统统绕过这片山。每每说到此事,老于的爷爷于老爷子,眼里的笑就意味深长。
老于把摩托骑来,有点不情愿:“蟒呢?”
熊建林指着对面山坡说:“你看,像不像?”
草木翻涌的痕迹正在盘旋而上,柔软的植被整齐摇摆像是在给谁让道。老于念叨,啥也不是,一回头见熊建林已经跨上了摩托,便追过去:“你小子就是让我来送摩托的吧?你可说了,骗我是儿子。”
熊建林把手里的韭菜花扔过去,说:“那就把韭菜花送给我妈。”
车轮在石子路上打个滑,上了水泥道。摩托开得很快,峡谷植被迅速后移,白云却挂在天上一动不动,有种视觉的错乱。一路走过,除风声外,还听到不知什么鸟在林子里叫,声音清亮得像刚融化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