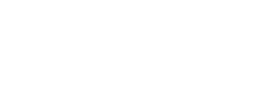前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乘地铁,坐过了一站。过了就过了,无所谓,我对很多事情都无所谓。这一站叫公园前,名字轻飘飘的,我一直想,叫“公元前”多好,这就不单是空间意义上的地名,而是一个时间意义的概念。出站的时候,我许久打不开支付码,后面站着很多人,虽然没有抱怨,但我很慌乱,好在终究支付完毕。出了站,外面猛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时辨不清身在何处,何去何从;刹那间,我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具体说,我突然像丢失了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并不太老,四十六岁,徐娘大半老。而这样的情况却时有发生,有时候我用手机支付或者扫码的时候,迟迟打不开手机的扫码位置。那时候,我看见我老公的眼神里有无限的怜悯。我老公最了解我,他很爱我,又不敢伤害我。
地铁站外,人潮涌动,身体纵横交错,穿梭密织,我孤独难当。世界在我面前快速流动,我的大脑也在惶恐地运转。此刻,我无助到了极点。我想问人:这是什么地方?又不敢。怕招来像我丈夫一样的鄙夷和同情。
站了半天,我才看到三个字:大马站。苍天,原来我在这里。我缓缓辨清了方向,认出了马路对面外星球一样的大马站十字地下商场,依稀看到了熟悉的北京路口和从墙壁上伸出胳膊的蜘蛛侠。我在人群中放肆地长叹了一声:唉——发现有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迅速逃离似的往前走。
我在恍然大悟,前行,心跳咚咚作响。我长嘘了一口气,再嘘一口气,总算安心了。在这密密麻麻的人流中,我一定是一个异数。我径直回家,上楼。
刚出电梯,猫听到了我的脚步声,长一声,短一声,在屋内叫。我心想,自己还不如一只猫呢,它都如此敏感,而我已经变得如此迟钝。开了门,猫缠着我的脚脖子,像自己的一个影子。我打开空调、换拖鞋、换衣服、洗脸擦脸,猫一直缠着我的脚脖子。接着我给猫喂食,它才安静下来。
这猫,像一个吉凶难辨的事物。
我接着开始做饭。不一会儿,我老公回来了。饭熟了,他坐在餐桌前,看了看我做的饭,说:“是米饭。”正要盛饭,他的眼睛盯着碗,盯了半天,也没说话,也不盛饭。我仔细看那只碗,没有洗干净,碗内有一小片残留的芹菜叶。我没动,也没说话。我在反思,已经好几次没有洗净碗了,每次我都非常讨厌自己。他没有盯着不放,只是投来一丝含有鄙夷不屑的目光,但他的眼神一旦和我的目光相触,他便旋即收回。他只是盯着碗,一动不动。然后,他悄然起身,默默拿起碗,进了厨房,洗,洗了半天。我听见他的手指在碗上面蹭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声音像老家骂人的土话一样,尖锐、凌厉、刻薄,那声音响了半天。他一直在洗,似乎要把那碗上的釉洗下来。终于,他停下来,接着又一手捏着碗,一手持着手机,站了半天,一言不发。我不声不响,嚼着寡淡无味的饭菜,那饭真是要淡出个鸟来。他终于出了厨房,坐下来,要盛饭,却又没盛,又拿着手机看起来。他看了很久,手指头在手机上摆弄,就是不吃饭。我早就放下了碗,看了他半天。他没看我一眼,我不吃饭了。我将筷子狠狠掸在碗沿上,筷子发出一声清响,像一个休止符。
屋内空气膨胀拥挤,墙体被压得弯了出去,快要爆炸。压得我喊出一句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明天去政务中心。这句话在内心里酝酿了很久。
他迟疑了一下,又以很正常的语调说,可以啊。墙体恢复如初,弯度修复。他像答应我去菜市场,或者去公园、去电影院一样,他也不问去政务中心干什么,只是无条件答应。晚上,各睡各的房。废话,我们早就各睡各的房了,都五年了。我一夜无眠,下定了决心。
次日上午八点,天已经热得像桑拿房,我和我老公出了门。在电梯旁,我们遇到了邻居,一个香港客,他高高的个头,年龄应该过了六十岁。我们互相点头致意,问好。我知道他要去香港上班,他每天都这样,风雨无阻,周末迟一点,平时他都是六点出门,开车,八点赶到香港,正好上班。而他今天却迟了,也许是睡过了,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和他寒暄两句,可我没心思。再说我一个女人,没必要那么殷勤多话。
今天我决定去办一件事,我老公很配合。这件事,我想了良久,还是去办了吧。这是一件临时决定却是长久酝酿的事,也是我们二十年来积累的陈年旧事。说实话,我内心并不确定这样办是否妥当。但事情是我提出来的,似乎是为了维护我最后那点轻飘飘的骄傲。
我们进了电梯,香港客看着我老公手里提的大笼子,笼子里装猫,他想要说什么,但最终没开口。他可能看到了我和我老公非同寻常的神色吧。猫在笼子里低低叫了一声,似乎有点恐惧。
电梯停在十九楼,双拐老头颤颤巍巍地进来,他的年龄最多比香港客大十岁,面色红润,五年前他出车祸差点丢了老命。他也没有孩子,孤身一人。他走起路来几乎是靠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最多在楼下的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就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偶尔和邻居说几句话。电梯到一楼,他没有下。我想和他多说两句话,可我实在没有心情多说一个字。
这天是七月的第四个周四,炙热的阳光猛烈地将所有的花催开了,鸡蛋花、羊蹄花、桂花、三角梅、异木棉、黄风铃等,路边落花成阵,好不凄惨。我不会开车,我老公会。我什么也不会。一小时后,我们来到户籍所在地政务中心门外,停好车,一前一后向政务大厅门口走去,他在前,我在后。到门口,他停下来说,你先进去取号,我抽支烟再来。他的语气平和,似乎和办理看病挂号毫无二致。可这一次,哪里是平常。
我排队,取号。排队的人很多,最前面的一对夫妻正向民政局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争相攻讦。后面还有五六对夫妻,轮到我们至少也要在一小时之后了,我耐心等待。我回头看,我老公还在大厅门外。我想好了,我只说一句话,看我老公怎么说,我绝对不多说话,我一定要速战速决,绝不拖泥带水。我的废话已经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会说偏了题,之前,我老公总是提醒我,你说的不是那个吗,怎么又说起这个了?后来,他不提醒了。我的话也越来越少。我想好了,今天我绝对不废话,不多说一个字。
半小时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这种情况于我而言,也是时常发生的。正如我总是在出了门,等电梯到来的时候想起一些事,灯还没关,电源没有关,水龙头没关,门禁卡没带、猫没有给粮,等等。我会下意识地将手伸进包内,清点一下随身携带的钥匙、手机、卡包等。这是近几年来惯见的事。
此刻,我忽然想起:不得了,猫还在车里。40℃高温,在密闭的车内,猫一定会被闷死。我想要让我老公去车里看看,他在门外;想发微信给他,又想绝对没这个必要,都到了这份上,还发什么微信,昨晚都差点拉黑他。想要打电话,更不必了,为了一只猫,让我给他打电话,尤其是此时此刻,简直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