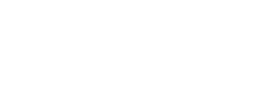一
条状的木盒子停在屋门口,很快就被抬进去安置下来。院门口聚拢着许多人,吵吵嚷嚷的。夜色笼罩下,篱笆影子看起来长短不一,正像是这些人各异的笑容。一时之间,男人们弹烟灰的姿态都变得不尽相同。
正屋的门大开着,冬夜的冷风直往进灌,使劲儿推也合不住。天空黑漆漆的,半点星子都没有,只是月牙缀在那幕布上,望久了,惨然得很。她悄悄地掩在门后,看见有人进门,身上随意披挂了件不成形状的白衫。顺着门缝的角度,她单能瞧见人的鞋底儿,还有妈妈不甚清晰的侧影。那新进的人似乎靠去了边上,带去一片影影绰绰的白色,一点声儿也没出。明明是最熟悉的屋子,竟叫她一步都不敢踏进去。
父亲去世的消息传过来的时候,秦晓琳正在公司里开会。坐的位置不高,尽管冷汗出了一身,但还得硬等两小时散会。
老人去得很安详,是隔壁刘婶在群里传的消息。家里另外三个子女陆续做出了点回应,秦晓琳匆匆扫过,从震惊和伤心里瞧不出什么错处。二哥已经上了回老家的高铁,另外两个姐姐估摸着今晚前也能赶回去。除了她和二哥,其他两个姊妹不在一个城市,过年才能有的团聚提前了三个月。
八十二岁离世,是喜丧。
上个月回去,元宝才把几颗红豆种进了纸杯,冒了点绿芽头出来,父亲就忙着帮她移植到花盆里。祖孙俩相处得很好,秦晓琳反而有点插不进去话。老人皮肤皱缩,面颊垮下来,法令纹处是两道深壑,很有不怒自威的意思。但小丫头丝毫不惧,她也瞧出,父亲眼睛里多数充斥着笑意,看上去比往日还精神些。
父亲的身体向来硬朗,最重的疾患还是前年的肺炎。住了十来天院,把元宝寄放在刘婶家里,他从第一天起唠叨到出院,陪床的二哥不胜其烦。这一支脉人多,又都有文化,算是孝顺,也从不短着老人每年的体检。长期以来,除了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病痛,连血压都能长期稳定在正常阈值内。子女们刻意不往后深想,但日子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所以悄没声儿去世这种事情,确在意料之外,引发的震惊反倒压过了哀伤。
两小时的会议坐凉了心肝,人却也安静下来。秦晓琳惶惶然地请假,恐一时半会儿批不下来,专门加了备注,亲人离世,烦请加急处理。半小时不到,经理回了电话,卡在她交接完项目资料的时候,时间刚刚好。
文件整理了一堆,包括一份烂了尾的策划,她没有明说要同事帮忙处理,只是单请人家参考。MCN公司靠着资源和创意吃饭,秦晓琳干了三年,没培养出什么电视剧里的白领气质,倒是染了一身讲瞎话的本事。他们办公室里寻常就是这样,烂摊子一个接一个,中途被新的事情盖起来,密不透风的,也算是过去了。偶尔和凯文谈起来,对方的附和顺不了秦晓琳的心意,她也懒得再论。泥潭里的人最忌讳再谈工作,轻松些的人也难能体味个中痛苦。
凯文是新加坡华裔,但大半辈子都在国内。华裔身份除了给他上学提供便利,在语言文化上没能造成任何影响,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交往了大半年,快走到结婚的最后一步。秦晓琳觉出对方要提见家长的事,便尽力装傻拖着,离得越近,就越烦躁。两个人相处还算有来有回,日子也可以过下去。但她习惯平时入夜先关灯,两个人摸黑亲热,惹得凯文不快。细细回想起来,他到现在还没见着她下腹的疤痕,遑论见到跟着姥爷一起生活的元宝。
事发得突然。她临走时给几个关系近的同事发了消息,又单独私信凯文,最近几天的午饭没法一起吃。一问,是回家奔丧,对面再没了消息。秦晓琳心里有些熟悉的慌张,还有新鲜的腻味涌出来。
手机没关,自虐似的等着。
待到一连串的人情交代好,又考虑到办丧事恐需人手,秦晓琳打算开车返乡。她从家里带了些洗漱用品,换掉上班穿的高跟鞋。全程都还算平静,却记不得拿了几样东西,来来回回重复了好几遍。翻找身份证很是花了一阵子,最后才想起来,恰搁在上回杭州旅行穿的大衣口袋里。衣服很新,父亲在家里还没见她穿过。
车里有股淡淡的香气。秦晓琳爱喷香水,老头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嫌的。每次她刚喷完,他都会离远些,散一会儿才慢慢正常过来。久而久之,她已经习惯回家不带香水,却没有意识到车里的味道早就携在了身上。
这会儿,秦晓琳想落下几滴泪来,但面颊是干的,心里却潮得像在河里浸了一夜。
二
天黑透了,她浑身也跟着冷透。忙碌的人们基本不理会这个小女孩,也并不在意这家里的其他人。她跟着姥爷住在乡下,不常见人,亲戚们简直都要忘了她。没什么人来,屋门背后愈加森凉,她便起身溜溜达达地晃悠,决心去瞧瞧前些天埋下的蚂蚁窝。老人往日常带她来这屋后的玉米地,偶尔能在夏天晚上捉住偷玉米的小孩。小孩们对此也并不慌张,因为老人只是笑着请他们带着外孙女玩。大些的小孩都不太瞧得上她,她便只管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追。追是追不上的,倒绊得一身泥,回来哭着求姥爷洗衣裳。
此时的玉米地黑黝黝的,风比前院还要大些,但她竟不觉恐怖。相较起未曾谋面的亲戚,自己辟开的小片土地要可爱得多。她开始想念故意让自己摔跤的小孩,想念姥爷在夏天随口讲的故事。家里的院子从不像今天这般拥挤,她也从不像今天这般沉默。冬季的寒夜来临,才叫人发觉姥爷的大树已经只剩枝头,像是一点绿色也不曾有过。
秦晓琳出生的时候,父亲的饭店已经颇有规模。她没能像大姐、二哥一样在乡村度过童年,也难得在节假日回村省亲。母亲比父亲年轻十多岁,罹患心脏病,早了八年去世,葬在了市郊的公墓。自此,秦晓琳更无机会返乡,直至父亲带元宝回去。出于这一原因,她才同老家的邻居有了些走动。
从本市开车回去,她比搭乘高铁的二哥迟了一步,匆忙打了照面。四十多岁的男人,这时候看起来面色发黄,嘴唇也泛青,不复几日前视频中的意气。乡邻来了不少,尽管不熟,但人人都想打听这子欲养亲不待的八卦。父亲惯常住在侧屋,进门前,秦晓琳捏紧了提包,不撩门帘,狠撞进来,却没见着遗体。随后的二哥拍了拍秦晓琳的后背,她僵直的身子骤然卸了把劲,冷汗涔涔。
住村头的堂哥一家帮了忙,已经请人把遗体挪去了殡仪馆。想象中的场景皆未发生,提前垫的勇气白做了样。秦晓琳说不清自己的感受,那个在村里开车也没减速的她已经软了一半,像是留个空壳专以示人。
出来,刘婶早就候着他们,道:
“亏得元宝睡得踏实,不然可真得吓孩子一跳。”
她把孩子领去了自己家里,正由大儿子媳妇照管着。二哥进门在柜子里掰了茶砖,拿到院里来泡。村里远亲不少,总也不能都干站着。秦晓琳看了他一眼,对方略微颔首。
“我今天进门给老爷子送早餐,人坐在椅子上,正对着大门口。我喊了几声没动,过来一瞧竟然是去了。”
“昨儿还说要找我们家媳妇来给元宝编辫子哩,这谁又能想得到……”
刘婶絮絮叨叨,脸上现出某种熟练的悲悯。秦晓琳心烦意乱,给人斟了些茶水,晃了几滴出来。
他们家的四个子女给刘婶每月四千块钱,父亲和元宝的饭钱都包括在里头。刘婶现在也没有工作,只是每天来三趟送饭,倒也乐意得很。但碍不住年纪大了点,嘴比旁人碎些,惹得院里村人都往过来看。
父亲上月主动联系了秦晓琳。电话里语焉不详,大抵是和元宝有关系的事情。她那时刚下班,耳朵和肩膀并用,夹着手机应声,不小心摔到了地上。手机没什么事,电话倒是断了。再拨过去,没通。逢周末也没什么事干,她干脆驱车回去看他。
只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车,秦晓琳就能见到父亲。说到底,总共才隔着六十多公里。他们过去关系很好,这两年反倒生分了许多。她很少回去,也不愿意主动过问元宝,像是避着些什么。似乎不去触碰那里,她就一直停留在二十多岁,没有元宝的牵绊,也没有把父亲拖得年老返乡,招来村人探究的目光。
岁月悠长,一米八的人撑上了拐杖,看起来还不如她高。秦晓琳进院的时候,父亲靠在树下的躺椅上,正逗着元宝拼拼图。石桌上摆着棋盘,零星置了车马,正正在格子中间。
孩子先看见她,怯怯地停了手。老人也发觉了不对,抬头瞧过来。他过去不喜欢秦晓琳穿得一身黑,总说年轻人该有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