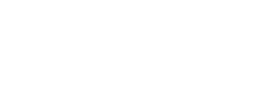他们都是用卫星电话导航来的。
她也是。
羊群走在我前面。背上的篮筐里装满了青草。我远远就看见一个人站在路边,脚旁边放着一个对她的身形来说可谓巨大的旅行包。走近了些,辨出是个女人。她低头看看托在掌心的手机,又朝我望望。那样子,是要等我再走近些好问话。我放慢脚步,抬头想看清她的模样。但即使走到她面前,我依然辨不清她的真实模样。不知道她看我是不是很清晰。我知道,我对她将会一直处于这最初的模糊印象。正如羊眼睛里的风景跟人看到的风景不会相同,男人眼中的女人跟女人眼中的男人肯定也不同。她抬眼看着我“哎”地叫了一声,又低头看手机,然后抬眼说,请问一下,这里就是拉达山了吗?
我说,这里不叫拉达山,叫茫然湖。
她抬头扫了一眼茫然湖,说,这就是茫然湖啊?就是个水塘吧。
我说,水塘才没这么大。
茫然湖的风吹拂着脸颊,带着一丝潮湿气息。她没跟我争论,忽然说,为什么地图上有,导航显示也已经到达,可这里的这些山一点也不像。拉达山到底是哪一座啊?
我说,听说过,没见过。我也在找。
她抬头惊讶地瞅着我,慢悠悠地说,你好像是本地人,这么说……你也没找到?卫星电话导航,怎么可能出错?一下说拉达山就在右边,一下又说拉达山就在左边。可这里却没山。她又对着手机一阵操作,我听见她手机里一个女人的声音:目的地就在你前面,此次导航结束。
女人颓然垂手看着茫然湖,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
茫然湖真的不大,大半天就可以沿着湖边转一圈。湖水东边的尽头是个巉崖,岩石裸露着,远远地看得出很险峻。背后是一带山峦,几条沟壑,冷杉林间忽然露出一片光秃秃的空地,也不知遭遇了什么。沟壑里的水都汇向了茫然湖。北边是个豁口,一条路弯弯曲曲不知道通向了哪里,但隐约可见不远处便是更高的山峦。西边是一带山峦,蜿蜒起伏,同样森林浓密。山麓与我家之间,是一大片农田,据说都是我爷爷奶奶开挖出来的。南边也是个垭口,是通向镇里的山路。这个女人就是从这条路来的。这时候,湖面上光斑碎影随波摇晃,夕阳下的湖水反光,有些刺眼。
她眯着眼睛转过脸说,这几天有人来爬拉达山吗?
我说,这几天没碰到过。以前不少。
她说,以前是什么时候?
我说,半个月以前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仿若自言自语道,不应该啊,导航上标得清清楚楚……难道拉达山真的只是个名字?难道那么多人想攀爬的这座声名远扬的山,真的只是个意象?她忽然抬眼紧盯着我,这里真没有拉达山?
我说,周围这些山,真的都不叫拉达山。
她茫然看着周围,那眼神像是要在山峦中生出一座拉达山来。这时候,茫然湖北边的水中映现出一道暗色山影,很像一条在水底扭着身躯蜿蜒而行的巨蛇。我听见她沉吟着说,看来我们都错了。都以为拉达山也像天下名山一样,坐落在连绵的群山间,有一个单独的名字,远远就见它高高耸起,山下长满了树,山顶白雪皑皑,天空有老鹰盘旋,半山腰白云缭绕。要爬上山不容易,山上多半是风化石,有巉岩高崖,四季积雪,不化冰川。从来就没人登过顶,还是座处女峰。据说还有神仙住在上面。然后就引来了那么多要登山朝圣的男男女女……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个模样模糊的女人。既然是神山,岂容这么多人轻易找到?嘿,一开始就错了……她在自言自语。此刻,我不再是她的交谈对象,而是个偶然听到她表露心迹的路人。
羊已经远去。我看了她一眼,紧走着要追上我的羊,草筐里的镰刀都晃了出来。我弯腰捡起镰刀,扭头朝她喊道,我家就在这里。我家吃晚饭很早的。你最好早点过来。
我知道她今夜没地方可去,只能在我家借宿。
小时候,我喜欢跟爷爷去放羊。放羊也用不着跑太远,几乎就是围着茫然湖绕圈。羊也不多,茫然湖边的草地足够了。后来,爷爷死了。办完丧事的那天傍晚,我伤心地看着被放置在旮旯里的草筐。爷爷每天都穿在身上的这件羊皮褂,被随手放在草筐上,盖住了一半草筐,我看见那把镰刀就躺在里面。草筐倚在墙角静静地立着,仿佛正在追思它的主人。父亲看我在盯着草筐,随口说,往后,放羊就是你的事了。
我就这样成了个牧羊人。
爷爷自称是个一辈子耽搁在路上的老不死的。他总是会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些我听了也似懂非懂的话。他说他就是听说拉达山如何神奇,才跑到这里来的,想要登上拉达山。可找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结果全落了空。当然也在这里遇到了你奶奶,但也难说是不是幸事了,他神情悠远地说,结果弄得这么大年岁了也没能上一次山,甚至都没目睹过一次拉达山的尊容。他浑浊的眼眶里忽然有泪水流出。
他看看我,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就这样耽搁在路上了。
爷爷说的这里,就是巴茅山深处的茫然湖边。这里冬天下雪,常年寒冷。地里的苞谷要长半年多,才会稀稀拉拉地有点收成,种植洋芋收成要高一些。茫然湖周围的庄稼、草木虽然都生长缓慢,但也枯朽得慢,即使到了寒冬,只要不被雪覆盖,那些已经焦黄的草叶仍然柔软细腻,羊们依然吃得欢。我家就靠茫然湖边的苞谷、洋芋和这群羊勉强度日。不是爷爷喜欢住在这贫寒之地,而是他一辈子都想登上拉达山。
至于父亲,他对拉达山从来没什么兴致。他说,那就是个虚幻的传说,你也信?但他好像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里。这些年来找拉达山的人越来越多。忽然涌进来的这些人拿在手里用的,塞进嘴里吃的,穿在身上保暖御寒的,都让他眼花缭乱赞羡不已;闲谈中那些人所描述的外部世界也让他目瞪口呆,难以置信;但依然没触动他想要去见识见识。也许他已经被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描述的五花八门的世界吓得不敢动弹,丧失了要走出去的胆量。
父亲正在喂羊水。他习惯在羊群归家进栏前,给羊们喂一些放了盐的清水。母亲在屋檐下抱着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崽查看。小羊咩咩地嘶唤,母羊着急地围着母亲转,又伸头拱拱母亲,生怕母亲伤害它的孩子。我穿过院子,扭头看见那个女人背着她那庞大的红色旅行包,正向我家大门走来。父亲看了一眼,冷冷地说,又来了个疯子。他把这些年来寻找拉达山的人统称为吃饱了没事干到处乱跑的疯子。
母亲扭头向门外看了一眼说,小羊的脚好像有点瘸,可能是被踩了。她放开小羊,看着小羊迅速奔向母羊,步态欢快,终于放下心来。母亲再次看向门外,忽然声音异样地大声说,今晚又有客人来了,还是个女客。我再去准备点好吃的。
母亲一直在为我娶媳妇的事担心,只要见到年岁与我相仿的女人,就会变得格外热情。妹妹听说有客人来,提着锅铲就从厨房里跑出来,一脸欢喜,因为又有人跟她同住,跟她聊天了。母亲接过妹妹手中的锅铲,匆匆进了厨房。
既然拉达山就在这里,那我就在这里寻找好了,我们站在院子里,她仰头望着满天繁星说。这是银河系,那个是北斗七星……这个地方叫巴茅山区,这座山峦叫达爱峰……周围这些山都有名字的是吧?可为什么拉达山就只有名字没有山呢?……只要诚心诚意,锲而不舍,总是会找到的。
她终于认可了这里没有一座叫拉达的山这个事实。虽然让她失望,疑惑,但好像也激发了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她说,古人诚不我欺。你说,他们骗后人干什么呢?
我说,他们杜撰那些稀奇古怪的事,也许不是为了骗后人,而是为了骗他们周围的人。后人看见,就信以为真了。
她看看我说,这倒是有可能。不过我还是相信他们所说的。你想,从古到今有那么多人来找,真是前赴后继不折不挠。你说,到底为了什么?
我爹说,是吃饱了没事干。
她笑了一下,不再说话,仰头看着繁星闪烁的银河。她脸上找不到拉达山的沮丧已然变成如水一般的平静。也许她真要用漫长的一生,来等待她想得到的结果了。地球上这个偏僻得没有任何标识、极少有人知晓的角落,这时候正有一个女人在极其专注虔诚地仰头眺望银河繁星。这一幕让我有些感动。因为此刻我也陪她一起仰头看了。繁星夜夜都有,但这样的时刻有生以来却仅有这一次。
在我家住下来的最初几天,她几乎每天都跟我去放羊。妹妹很想跟我们去,但被母亲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妹妹噘着嘴朝门口的公鸡踢了一脚,公鸡惊叫着扇动翅膀跃开几步,生气地昂头向着妹妹“咯咯咯”,权衡着要不要发起反击。妹妹不理公鸡,气呼呼地拿起一把镰刀,独自出门到苞谷地里干活去了。
我身穿羊皮褂,肩上挎着草筐,里面放着镰刀,穿过院子,打开羊栏门。
我妈有些伤感地说,你这副样子,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我没理她,站在门口看着羊们鱼贯而出。我既要清点羊,也要看看羊是不是都健康,那几只母羊是不是会下崽。等最后一只羊走出羊栏,头羊已经在大门外了。那个模样模糊的女人站在大门外一侧,饶有兴致地看着羊群,又看看我,拿不准要不要吆喝一声或者要把羊朝哪个方向赶。她见我漠不关心,便站定不动,任由羊群自己向前。
我走近她时,她说,羊知道去哪片牧场吗?
我说,这里一出门就是牧场。它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她说,你也不管那里的草好还是不好?
我说,草好不好,它们知道。跟着走就是了。我放羊,就是打发一个又一个日子而已。
她以那副再三斟酌的神态看着我说,到底是你在牧羊,还是羊在牧你啊?
我说,不都一样吗?
她说,那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啊?
我说,走吧。跟着我就晓得了。反正今天有你跟我做伴。
她说,你咋不说是你跟我做伴呢?
我说,那不也是一样吗?
现在正是夏末,茫然湖边的青草越来越旺盛。微风吹拂着,茫然湖波光粼粼。头羊带着羊们从茫然湖右岸向前。我和她懒懒地跟在羊群后面,打发这个跟以前一样的日子。湖面上看得见一群野鸭。冬天会有黑颈鹤来过冬。几只鸟惊叫着从羊群前飞起。我看见有两只野兔从远处奔过。她也看见了,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扭头看见我漠然的样子,就噤了声。野兔也是我的老朋友了。可今天只见到两只。只有父亲会隔三岔五跑到这一带来捕捉野兔。他说它们会糟蹋粮食。这里就没种粮,他是在跟天上盘旋的老鹰抢兔子肉吃。经常在湖边活动的还有一群岩羊,也许是黄羊。它们不知道家在哪里,也许就在东边的巉崖上。至于那些老鼠,它们习惯在湖边草地上到处挖洞。
羊群在吃草。我把羊皮褂铺在草地上,让给她躺。我直接躺在草地上,手臂遮着直射的太阳,听忽大忽小的风,听对方的呼吸声;看天空盘旋的鹰和不时飞过的鸟,看忽聚忽散千变万化的云。有一阵,我知道她睡着了。然后我也睡着了。醒来后,我们跟上了自己的羊群。但在下午回家之前,我每天都需要割一大篮筐青草,背回去晒干储藏。
第三天,我们依然躺在草地上看云。我问道,你哪天走?
她说,谁说我要走?在这里放羊多好啊。既然都是放羊,跟着你放你家的羊,还不如我也去买一群羊来,放我自己的羊。
我笑了一声。她不置可否地看了我一眼。
第二天一早,我家人发现她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在妹妹的房间门口看了一眼,她那庞大的旅行包还放在地上。我还是若有所失地独自放了一天羊。
当天晚上,她也没回来。第二天中午,我还在茫然湖北岸,忽然看见我家附近来了很多人,还有很多驮着东西的骡马,不知道她买了些什么来。难道她真要在这里住下来放羊吗?我心里一阵狂喜,很早就赶着羊回家。远远地,我就看见靠近我家的路一旁,已经堆放了一堆建筑材料。
看来,我放羊真的有伴了。
十天里,她找来的那些建筑工人就在离我家两三百米远的路边,搭建起了一幢三间平房和一个彩钢瓦做顶的羊栏,在茫然湖边非常醒目。放牧归来,我趴在她的羊栏边看了一眼,里面空荡荡的。我笑道,你的羊呢?
她说,羊栏都有了,还怕没有羊吗?明天这栏里肯定就有一群羊了。你明早出门,别忘了叫我一声。
第二天早上,我身穿羊皮褂,肩上挎着放了镰刀的草筐,赶着羊群经过她家门口时,果然从她的羊圈里涌出一群两只大耳朵盖住了两侧的半个脸的羊来,虽然比我家的少,但都是没见过的品种。我看见她身穿一件塑料雨衣,背着一个竹筐,手里拿着根竹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