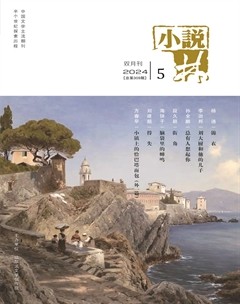1
除夕那天,大舅是在我家过的。
中午的时候,家里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里面不乏熘肉丸子、软炸虾仁、拔丝山药等。我爸从酒柜里把两瓶高档白酒也拿了出来,看来今天他老人家是要跟我大干一场。
这之后,就在全家的一片热热闹闹中,大舅来了。
自从拆迁以后大舅和我爸妈住同一栋楼,过来方便。前两年我舅妈去世,他一直忙着找后老伴儿,我妈心疼她这唯一的弟弟,也经常叫他过来吃饭。
“你吃了没有?来这儿吃吧!”我妈总是给大舅打电话这样说道。
因此,那时我每次回父母家,基本上都能见到大舅。尤其是最近,他来得更加频繁,并且每次过来百分之百都会谈到他跟女儿要钱的事。大舅家拆迁后分了几套房,另还有四百万的拆迁款,表妹和她那口子——名叫何奎——钱都自己拿着。一开始大舅也无所谓,但是自从他开始找后老伴,渐渐地发现这件事没钱不行,就想从他们手里要回自己的那份儿。
然而,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闹了好几次,可每次的结果大舅不是气呼呼地就是跑过来哭。
我表妹原来在超市收银。她很胖。夏天的时候,她总是戴着一个遮阳的帽檐、斜挎个小包赶公共汽车前往超市。每次下班回家,她都要先在沙发上静坐半天,让那胖胖的身体向四周呼呼散发着热气。
只见她面容阴沉地坐在那里,脸色红红的,在向四周散发热气的同时,她也在呼呼散发着怨气。
“你这个有钱人!”这是她当时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说的时候一脸羡慕。
当然了,那是从前,拆迁以后表妹就不再这样说了。她也不再去工作——就让别人去工作、去挤公共汽车吧!然后把房租交给她。饭也可以不做,手指在手机上点点,片刻之后一个外卖小哥就会一溜儿小跑地把食物送来……
现在的表妹,变得更胖了。
表妹的那口子何奎原先在小区物业上班,负责维修。自从大舅家拆迁,他也悄悄地辞了职,终日在家里打游戏。听说,他是嫌弃自己的那份工作不够体面。
他们的新房刚下来正在装修的时候,我过去看过。见到何奎还特意在客厅里砌了一道矮墙,成“L”形,靠着房间的一角形成包裹之势。那就是他以后的“工作间”了,将来便可以坐在里面心无旁骛地打游戏。
后来大舅过来,我妈问,何奎上班了没有?
大舅轻叹了一声,说,他上什么班啊?一直在家里待着呢……
这句话大舅像是有意说给我听的,因为他早有让我在单位帮何奎找个工作之意。不过,我才不愿意帮他。现在看大舅又这样说,我照样就当没听见,眼睛转向别处,还是看看我爸妈家阳台养的花吧!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有红有黄,还有一朵粉的……真是俗不可耐啊!
自然,以上所有这些变化的最开始,就是那次拆迁。
当时的政策特别宽松优厚,不光户主有房,连户主的姐妹也有。因此,我妈也分得一套,并且和大舅选在了同一栋楼。
表妹也选在了这栋楼,三户人家,三个单元。
乔迁之后,大舅家瞬间就变得又有房又有钱,小康的日子眼看已经开始。可谁想,在搬入新居还没一年我舅妈就总喊胸口疼,后来查出了癌症。两年以后,她就在无比的痛苦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她最后已经骨转移,疼得直喊妈。
“妈啊!带我走吧!我不在这儿受罪了!”
舅妈就这样死了。
葬礼那天,人们聚集在大舅家的楼下,几张桌子已经支了起来。舅妈生前的那些亲戚朋友纷纷赶来,送舅妈最后一程。
算下来,舅妈真是没过过几年好日子,刚刚有了点儿钱,就走了。这让所有人都不胜唏嘘。不过也有人说,那是钱一下子多起来自己“压”不住……那天早上,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喝着茶,一边就说着这些。这时,迎着初升的朝阳,我爸骑着一辆小小的电动车,左右车把上各挂着一大兜子的早点,快速地向我们而来。
事实就是这样,葬礼当天所有的一切——找大巴车、联系火葬场、饭馆订饭,甚至这天早上的早点,都是我爸操办的。而之所以如此,是我大舅根本没有一点儿办事能力。按我爸的话讲,你大舅就侃大山行,一到真格的就 啦!
可是,大舅不成,那何奎呢?他不是大舅家现在的顶梁柱吗?他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就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似的。
何奎这人话很少,还经常笑眯眯的,但心里的想法比谁都多。想当年,我还因什么事带他去过自己的单位。来到那高大的大堂,他眼睛都不够使了,脸上却还在极力地控制着,仍然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从那儿以后,他就变得别别扭扭的,好像什么事都要和我比个高下。比如节日家庭聚餐时谈论什么话题,我说完正在笑,就看到何奎欲言又止——他的上半身甚至都挺起了几厘米,喉咙在极深的深处发一个音,但是紧接着就又矮了回去,脸上还莫名其妙地带了股怒气。一会儿吃完饭,大舅正和我说话,他什么也没说,推门就走了。
正巧那段时间大舅让我给何奎找个工作,我就故意拖延下来。后来大舅家拆迁,何奎也瞬间变得“身价倍增”,我也就再不提给他找工作这件事了。
就让他天天打游戏吧,也挺好。
说回葬礼那天。
那天,我爸把早点买回来之后,人们就开始吃。
我也拿根油条在啃。无意中一抬头,正看到何奎在不远处吃着包子。他腮帮子鼓着,一个包子已经往嘴里塞了一半。我知道,这么些年来他对我的那种别扭一直存在,并且我给他找工作最后不了了之他也一定能感觉得到。刚才在屋里我们离老远碰到,我还伸手主动跟他打了个招呼,而他只眼睛一斜,头几乎看不出来地一点,就算是回应了。
何奎嚼着包子,就像有某种感应似的,也立刻向我看来——眼神中还带着一种不屑。
我赶紧调转目光,看向了别处。
2
除夕那天,大舅落座,我们开喝。
我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杯,看到大舅喝得很慢,我和我爸半杯都下去了他才喝掉浅浅的一层。
席间,众人先扯了点儿闲话,等到一杯白酒下肚,大家自然聊到了大舅找后老伴儿这件事。
舅妈去世已经快三年了,真快啊!在这三年里,大舅就从没有停止过找后老伴儿。
“电视里的相亲节目怎么说的?”那时大舅开始大量地收看此类节目,看完就来我家神侃,“厨房有烟火,客厅有笑声,卧室有爱情!嘿!你瞧瞧人家说得多好啊!”
他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就好像他能立刻就找到一个似的。
大舅和我舅妈的感情一般。两人虽然不吵架,但舅妈对大舅一直非常冷淡。据说那是因为她在外面有情人。就这样,两人在一起毫无滋味地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特别是近些年,舅妈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大舅日夜陪护,没过过一天踏实日子。现在舅妈去了,大舅不再有障碍,他终于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经人介绍,大舅前后见过不下十个,但是最终一事无成。所有的相亲都迅速地失败,最长的一个对象也没超过仨星期。对方不是嫌大舅长得难看就是一听说他自己不掌钱便再没了下文。想想也是,不光拆迁款,就连大舅家原来的存款也都攥在表妹的手里。每月大舅只靠自己的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过日子,有什么大的开销都得手心向上跟女儿要。这样,别人还嫁给你干吗?大舅还老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长相,可这重要吗?按照别人的观点(那也是一个因拆迁而暴富的人),要是有钱,别说长得难看,就是缺鼻子少眼睛也没事。更何况,在我看来我大舅长得也不难看。
后来,经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这一个终于成了。
此人年纪有五十多,十分时髦,早起化妆就得一个小时。我看过照片,见她脸上的粉很厚,特别妖冶。她还会炒股,且数额不小。
在此人的打扮下,那一段时间大舅也明显“潮”多了。比如,她给大舅买的一条裤子七百多,T恤也是名牌,而且还是粉色的。再配上一副茶色墨镜,我觉得大舅都有点脱胎换骨了。
“佟佟,你看看大舅的这身怎么样?你‘新舅妈’给我买的。”在我爸妈家,大舅特别得意地对我说。
“啊!不错不错!”我哈哈大笑。
大舅咧开大嘴,也笑了起来。
他告诉我,我这个“新舅妈”会疼人儿,而且不在乎钱,尤其是舍得给他花钱。还说她生活上挺“讲究”,化妆品摆了一架子,没事还爱喝个红酒……大舅连说带比画,上半身早就挺直了,感觉屁股随时都能从凳子上弹起来。
一般情况下,大舅聊天抡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插不上嘴。我也只会说“是是是……您说的是是是……”而我爸,则在一旁含笑不语,有时我们爷儿俩还会笑着对视一眼。我妈呢,可能在一旁正忙着准备午饭,不时地会问大舅一句:“那女的靠谱吗?你留点儿心眼,别让人给骗了……”语气中不乏一丝担心。
只有这个时候,大舅才会平心静气地说上一两句,但是很快,他就又侃上了。
“你大舅又牛了!”大舅走后,我爸说。
我大笑。
……
大舅和那女人同居了。
两人一开始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大舅做饭,女人炒股,外带捯饬自己,平常还拉着大舅这个“莱斯”那个“Mall”地逛商场。她的眼光还不错,大舅说自己长得丑,她却说,你哪里丑?在我眼里,你就是美男。
这里我得提一句,大舅已经和我那原来的舅妈有几十年没过过夫妻生活了,土地早就干裂缝了,所以(这样说虽然不应该)我很好奇他们两人的第一晚……那一定是地动山摇吧?
那一段日子大舅都乐呵呵的,有时来到我父母家还戴着他那茶色的墨镜。我一看,这哪儿是大舅,这不飞行员么。紧接着,不用二两酒下肚,他就又喷上了。
“佟佟,这回我算知道什么叫‘爱’了!”大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告诉我。
我再次笑起来,恭喜大舅。
没办法,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和我爸又得坐在下面当观众了。然后等大舅走了,我爸会哭笑不得地来一句:“这回他算知道什么叫‘爱’了!哈哈哈!”
鉴于此,所以后来我一听说大舅要来多少都会感到紧张。
“一会儿你大舅来。”我妈告诉我。
“……啊,又来啊?”再一看,可不是,今天的午饭比哪一天都丰盛,我父母家的厨房已经有点热火朝天了。
“怎么,你不愿意啊?”我妈语带不满。
我赶紧说不敢,然后再玩笑一句:“您什么时候能像招待我大舅那样招待我一回?”
“我招待你还差啊!”
很快,大舅来了,然后就是三句话不出他就又眉飞色舞起来。自己聊痛快了,满意了,这才会迈着小酒后微醺的步子回到家去。现在那里才能称作是“家”啊,里面有个女人在等他。
俩人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一个月,之后的一天,大舅跟表妹要了六万,一股脑儿全给了那女人。
“拿着,这是咱们今年的生活费。”
这是他们之前就说好的,俩人的生活费每月五千,全部由大舅承担。
结果,在拿到这笔钱之后,那女人就走了。
她说回去收拾东西,便一去不返,连同那六万块钱。究其原因,当然还是老生常谈——大舅不能掌握自家的财政大权。据知情人士讲,那女人应该早就知道大舅家拆迁后有不少钱,本想是来过奢侈日子的,谁想只有这每月的五千块。她本来还要再“观望”一阵子,但最终无望——大舅肯定是要不出钱来的。实际上,关于这些钱他后来连提都不提——正好现在有这六万,她就走了。
“你那么着急给她钱干什么啊!”事后我妈也埋怨大舅。
此刻,大舅早就没了当初的得意,他搓着他那双粗大的手,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六万,不是小数啊!你告诉我她住哪儿,我去给你要回来!”
“算了吧……”大舅终于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