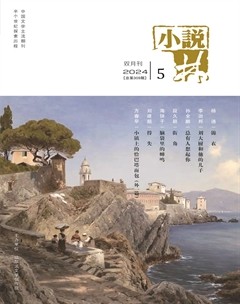一
我正在家里看电视,老家将军寺村支书老汪叔打电话说:“我来城里了,你在哪里住?找不到你家了。”幸好以前回老家时加了微信,我赶紧给他发了个定位,随后又发了几个字:十三楼东户。二十分钟后,听到楼梯处有人在说话:“是这里吧?”另一人附和道:“是,以前我来过,好像就是这儿,这不是门口还有小孩子画的恐龙吗?”我知道老汪到了,就起身开门。人还没进来,提溜着的红薯和粉条先进屋了,老汪随后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头发乱蓬蓬的,黄黄的。
我客气说:“叔,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
“也没带啥,自家种的红薯,打稀饭吃起来面着哩。这是我侄子。”他转过身子,“快喊叔,你这孩子怎么不说话?”那“黄毛”低声地喊了一声“叔”,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低着头开始摆弄手机。手机里的世界确实诱人,有时候他也拍拍照照、录些视频,我感觉现在的孩子都是让手机害了。我给老汪叔让烟,老汪接过,双手捂兜子,在裤兜子里找到了打火机,啪啪打了几下,火没着,甩了甩又打了一下,打火机才着火。
前几年老汪找过我一次,当时我正在开会,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我没有接。电话又响,我又没有接。电话再一次响的时候,我气呼呼接了,以为是推销电话,还没有骂出去,电话里一阵着急的声音:“我,我是你汪叔,将军寺村的。”略停了一下,继续喘着粗气着急地说:“车被查了,你赶紧想想办法,拉的一车白萝卜送不出去。”在城里我也不怎么认识谁,车违规要找交警,平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交集,想不到要找谁。
想了半天,我才想到了单位热心人太极拳师程书,他认识的人多,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后,程书马上说:“你等我消息,我问问。”不一会儿,程书回过来电话说:“你给李队长联系,去找他,带上钱。”他还特别交代别少了礼路。我连忙把电话发给老汪,又把电话拨打过去,特别安排一番,带上几百块钱。一个小时后老汪来电话说:“解决了,花了三百块钱。”电话里他一个劲儿表示感谢,“多亏了你,要不肯定要耽误事儿。”我心里一阵难过,也没帮上什么忙,凭空还让他花了那么多钱。那年过年回家,听村里人夸我可有本事了,在城里遇到事了也就一个电话。我听了,心里一阵惭愧,不敢正眼瞅别人,心里虚得慌。
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事,我等待着老汪说话,不知道他要干啥。“黄毛”依然在玩手机,两人谈话跟他没关系,他像一个局外人。老汪说:“你现在得回老家一趟,主持主持村里的大局。”我笑了,吐了一口烟说:“我能主持什么大局?还非得要我回去。”老汪面色凝重,烟也不吸了,手夹着剩下的半根烟:“你老曾奶奶不在了……”
屋子里的表“嗒嗒”向前走,停一下,又往前走。我心“咯噔”一下,为老曾奶奶感到遗憾,好人不长命呀!上次回家看她,身体还算好,记得当时老曾奶奶为了证明身子好,她拄着拐杖还往前刻意走几步,开玩笑说:“我还能再活一百年哩。”这才有多长时间,怎么说没就没了?
叹了一口气,我压低声音说:“汪叔,谢谢你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但主持大局还是让别人吧,我不够格。”
“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够格你就够格!其实,你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要打电话找人。”老汪叔身子坐正,一动不动,拉长了脸,眼睛直盯着我。那声音异常严肃,不容许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二
给媳妇打电话说明情况,简单在家收拾一下,我就和老汪叔回老家了。县城离将军寺村不远,“黄毛”开着面包车速度很快,车像一匹奔腾的小马在柏油路上飞跑,路两旁的树一棵接一棵往后移动。我呆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两边的风景向后都化成了历史,刷刷的景色在我眼前闪过,一棵树又一棵树,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真的,我想老曾奶奶了。
老曾奶奶年龄好记,今年应该有七十四岁了,她与共和国同龄。将军寺小学走出来的学生都知道,当初多亏曾老师和丈夫张军老师,方圆十来里的孩子才能上成学。那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军老师还是民办教师,他吃过没知识的亏,看到学校破烂不堪,就下决心要把学校建好。张老师和曾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里还在月亮光下做砖坯子烧砖头,下决心一定要盖好学校。那年夏天雨下得比较紧,路上的泥路遇上水,人站在上面像抹了油一样滑,他们在拉砖时刹不住车,架子车翻了,当时就砸在了将军寺沟里,张老师倒在了血泊里。曾老师和闺女拉着张老师赶到镇上医院时,一切都晚了,张老师还剩下一口气就是咽不下,看见母女俩无主的样子,眼睛里滴出了泪:“学校……建下去,那是村里的命。”曾老师点点头,闺女趴在一旁嗷嗷直哭。
后来,曾老师多次对村里人说:“他的命就是我的命。”张老师走后,曾老师没有离开将军寺村,她留了下来,继续建学校,她要完成任务。学校总算建好了,那四间房子费了不少周折,曾奶奶从此腰也弯了下来,再也直不起来,但她当老师却是好老师,学生们都听她的。
那时候,我家里穷,经常去放羊,其实也就跑着玩,曾老师劝我爹坚持让我上学。我家里条件不好,靠爹种点西瓜挣个小钱,上不起学,家里穷怕了。其实,我的脑袋瓜子好使着哩,不笨,用村里人的话说转得快,成绩基本上都是前几名,曾老师也说,考上镇一中没问题。我不上学的第二天,曾老师就来了。家里只有我生病的奶奶,一年到头躺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呻吟着、发呆、叹气。她没找到我,最后在我家的西瓜地里找到了我,我正在西瓜地里薅草。
“家里穷不要紧,”曾老师说,“我替孩子交钱,孩子不上学咋办?”
我听到这话,手一直在挠头,我想去上学,但爹苦瓜一样的脸让我暗淡了下来。
爹坐在半截砖上歇息,深吸一口烟:“家里没人干活不行,你也知道他娘是啥样子,家里真不中,我这肩膀扛不住事呀!”我爹不看曾老师,又接着说,“我也着急,没办法,人穷得慌,这草都长疯了。”
曾老师望着地里一人多深的草,想了想说:“我给你解决,但你得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当天下午,曾老师带领学生到我家地里,给学生每人分一垄薅草任务。把草都薅完了,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我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小孩子内心都不复杂,你心里对他好一点儿,他马上就感受到了。
那年的雨水大,西瓜没怎么结,几亩地的西瓜严重减产,收成不好,爹没说不让我上学,但就是不交学费。曾老师二话没说就为我交了学费。我爹平时啥事不说,但心里啥都明白,他让我端着一篮子鸡蛋给曾老师送去,曾老师又让她女儿红梅送回来一篮子油果子。坦白地说,那几年我和红梅关系不错。红梅喜欢玩水,她爹在世时经常带着她到将军寺河里去捕鱼。红梅总爱吓唬我:“水里有鬼。晌午头,鬼磨油,到了晚上黑,鬼就拉车了。”我仿佛看到河里面的水冒出来了一个三个头四只眼的东西,张开滴血的嘴巴露着尖尖的牙齿正向我走过来。看到我吓得不敢往前走、一动不动,就抿着嘴笑。我们两人顺着河转了一圈,影子在将军寺河水里跟着我们走。
我和红梅后来分数远超过镇一中,考上了县一高,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到县一高上学。据老辈人讲,这以后考上大学肯定是没问题了。高考前两个月,一次星期天放假回家,红梅出事了。当时我和红梅坐公交车回去,我下车去买两块冰糕,当我拿着两块冰糕回来时,停在路边的公交车被一辆大货车撞翻了。公交车翻了几个跟斗,红梅的身后盛开了一地的梅花,当场没命了。我眼睁睁看着红梅消失了,拼命地呼喊。
村里人说,从那时候起,在曾老师的生命中,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她一个人就守在将军寺村那个地方,再也没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