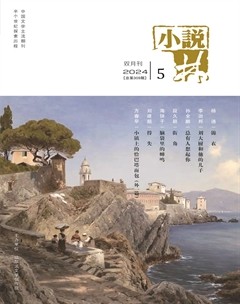有人说,“80后”一代是中国最后一批具有乡土情结的人。如果这句话成立,我恰好就是其中的一员。许多年里,我见过太多的人一面渴望离开故乡,一面却又眷恋着故乡。有人比我年长,有人与我同龄,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我们一旦谈论故乡,出走和离开就是最为强势的主题。
在急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好像离开就是正途,是心安理得,是顺其自然,而我们就忽略了回乡的情结。但一定有一些人,心里始终有一个回乡的夙愿。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有好多人在城市生活,但每逢春节,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农村。我们围炉喝酒,高谈阔论,回忆往昔,确实是无拘无束,遍体通畅,这种放松和自在与城市生活完全两样。
我也是不断地离开,做了八年乡村教师,然后去了县城,又八年,又去了市里。这期间,我有三次机会完全可以远走高飞,彻底离开故乡,但我始终在回望,在纠结,所以离开得并不决绝。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回来,他们该以怎样的方式回来?
在不断地离开中,我发现,返乡其实是大多数人心里隐秘的一条主线。有人风风光光地回来,有人平平淡淡地回来,而有一部分人,出走数十年再未踏进故土一步,不是不想回,而是不能回,他们将故乡撇在身后,而故乡也将他们彻底遗忘了,两两相欠。
回乡不一定是将肉身安放在故乡,精神的回归其实更为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衣锦还乡”,追求“荣归故里”。很多人被这样的主旨困住,当他们真正面对故乡的时候,反而心生畏难。而事实上,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是最为普通的一员,在城乡剧烈变化的激流中,衣锦还乡或许是每个人一生努力追求却又无法逾越的魔障。谈不上成功或者失败,但故乡最终都变成了一些人回不去的故乡,因而与故土隔离,与亲人疏远。
我有一个收藏家朋友给我的触动很大。早些年,他做煤矿生意、做酒店生意,风生水起,一时风光无两,我没有参与过他的风光,却深刻地见证了他的溃败,而他在跌落到谷底的时候,却做起了收藏。他要复盘,要重整旗鼓,要体面地回乡,但难度极大。于是,我便写了《锦衣》这个故事。
前几年,我以一个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视角,连续写了五个这类题材的中篇小说。写“我”在箭子川与众人格格不入,寻衅滋事,最后在众人的逼迫下,“我”的父亲将“我”带到城里丢了。父亲丢了“我”之后,又于心不忍,将“我”的四个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哥哥们的家庭住址写在牛皮纸上交给了“我”,“我”于是踏上了寻找哥哥们的旅程,也见证了哥哥们在表面繁华下的无奈和不堪。父亲引以为豪的“五虎上将”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无法回到故乡,每个人都渴望一件“锦衣”,可所谓的锦衣之下,满是心酸之泪。
二哥在表面的风光下,负债累累,他想尽一切办法拯救企业,可最终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只好想出了通过古玩生意募集资金的办法,但他还是功败垂成,再一次远走他乡。故乡成了回不去的虚幻之地。
“我”与老高被迫离开故乡,但我们也想荣归故里,我们被裹挟在二哥的计划中身不由己。正如老高所说,我们都是为了活得更好,有什么错呢。
我们常常因自己的认知而被困在原地,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头去看,却发现,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其实仅仅是你的一厢情愿,而他人并不关心,就像我们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毛病在哪儿,但我们会因此而更加在意别人的眼光,这种困扰放大来看,却往往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你所追求的锦衣,在别人眼中不值一文。但世间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透,却做不到,嘴里说着放下,心里却在负重,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