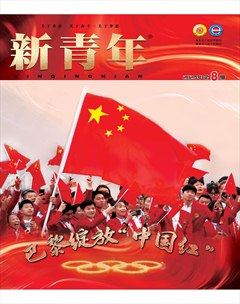1194年,芒种时节,喜降春雨,乡民小麦丰收后,忙于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到处是繁忙喜悦之情。
陆游身处这般情境,年高,辄有恙,身卧竹床,衰发不梳,但他常日的触觉、听觉、嗅觉、视觉随情而变,他享雨凉、听鸟鸣、闻幽香、看黄莺,在丰收和忙种的情境中,没有了担忧与愁绪,心愉而歌,举觞而饮,他是乐乡民所乐,共享喜悦,轻松愉快,他写《时雨》一诗: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老我成惰农,永日付竹床。衰发短不栉,爱此一雨凉。
庭木集奇声,架藤发幽香。莺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
即今幸无事,际海皆农桑。野老固不穷,击壤歌虞唐。
这是多美的一幅农家图,情景交融。一个“永日付竹床”“衰发短不栉”的老人,仍情系乡民,关心乡民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命运与共,是忘我,是无私。不同的经历与理想,不同的文化特质,在他诗中表现为这般不同的精神境界和特有的生活情趣。
他晚年,虽有终生的遗憾和诸般无奈,却化入了他的达观;虽有看穿人生的感悟,却无悔无愧;虽有贫困、病衰,却不作茧自缚;虽有愁苦之感,却不堕于悲戚;虽知来日无多,却畅然面对。
他咏叹自我的诗作中,辄有往事之思,有对沈园的不灭回忆,有对众友人的感佩缅怀,有对恩师曾几、考官陈子茂的深情悼念。
毋庸讳言,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陆游亦有内心的感伤与痛苦,这是灵魂的自白,这无损陆游诗词的光华,反倒让我们深度认识陆游是生活在烟火中的血肉丰满的诗人。他的诗作中,令我们过目不忘的是他的家国情怀,是他那辄入笔端的豪情,是他戎装走过的地方,是汉中、南郑,是大散关、骆谷,是和军卒 “行行重行行” 的山路,是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中原未复,壮志未酬,是他的终生遗憾:“可怜万里平戎志,尽付萧萧暮雨中。”(《夏日杂题之六》)但他不因中原未复而放弃,也不因壮志未酬而改节,“万事忘来尚忧国”,仍是他的坚守。他在垂暮之年,已知“墓木拱”,来日无多,不过他心中挂念的仍是 “何时青海月,重照汉家营?”且读他的《北望》:
昔我初生岁,中原失太平。
宁知墓木拱,不见塞尘清。
京洛无来信,京淮尚宿兵。
何时青海月,重照汉家营?
陆游放舟水上,赏朝云,观夜雨,访寺问僧,听渔歌菱唱,亦可消愁舒愤。他内心的隐痛,常常化为他的怆然之思。
一次,夏秋之交,在梦笔桥畔,他系船夜宿。残灯耿耿,潮声阵阵,不成眠,想起古人伍子胥,吟绝句一首:
梦笔桥东夜系船,残灯耿耿不成眠。
千年未息灵胥怒,卷地潮声到枕边。
到枕边的岂止是卷地而来的钱塘潮声?春秋时期,伍子胥以远见,规劝吴王,莫攻齐,应灭越,否则越必灭吴,“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吴王听信谗言,几怒,反赐伍子胥死。死前,伍子胥嘱人剜出双眼,悬东门,以看越军破城灭吴,亲眼验证吴王决策的亡国之误。伍子胥自刎,吴王命投之于江,江水怒翻,传说钱塘江潮是伍子胥未曾平息的千年之怒,而今,陆游中原沦陷之怒,又何曾平息?枕边潮声,触动他深埋心底的初心!“旧学成迂阔,初心堕渺茫”,“皎皎初心置天地,競兢晚节蹈渊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