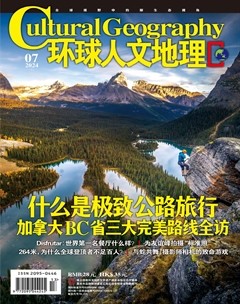杂面,此时念作cha面。九寨沟自古以来就是秦蜀交界,藏汉融汇。民国时期,以盛产鸦片闻名周边,川、甘、陕天南地北各色人等到九寨沟赶烟场,发鸦片财。说是赶烟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冲着鸦片来的,用现在的话讲,冲着因鸦片产业形成的资金流、物流、人流而来的。解放后,因茂密的森林资源,国家从较早解放的东北林区等地抽派大量人员,兴办森工。森工企业的人,虽然生活在他们相对闭合的圈子里,自给自足,与当地人交往不多,但在特定的时期,也算是九寨沟最富足的人群。解放初期,一个人口不过三两万的地方,习俗之杂,口音之乱,可想而知。倒是应该了这个杂字。
黄豆即大豆。当地一般不成片地种。我记得,生产队上好的水地,种玉米时便套种黄豆。一行高高的玉米,一行低矮的黄豆,看着好看有起伏。老师在小学教室里正经地讲过农业八字宪法,现在还记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我一直认为这样种法是按照其中的密字来进行的。我渐渐长大的那个生活圈子,没有人将黄豆叫做大豆。就是能听懂《在松花江上》那首歌了,也不知道东北的大豆便是九寨沟的黄豆。直到今天,我还在怀疑黄豆里能榨出油来?所以一直不喜欢大豆色拉油,总觉得没有从小吃到长大的菜籽油香。前几天,杂志社一同事说他老家种了两亩地的油菜,周末要回去收割。我说,两亩地的菜籽榨成油,你家也吃不完,干脆我们杂志社的人团购。
黄豆拿在手里,亮晶晶的。之所以亮,是因为壳坚硬得很。先要将黄豆蜕皮之后,再磨成面粉。黄豆面绝对是高营养,只是这黄豆面必须与其它粮食混在一起磨成面,才能煮出既营养,口感又好吃的饭食来。单纯的黄豆面,我没吃过,也没听说过怎么吃,想必营养太高,人体不易吸收,便没了如何吃的做法。说是营养高,可怜的却是,需和其它粮食一同磨才好。与小麦混在一起磨,名字叫做麦杂面。与荞混在一起磨,名字叫做荞杂面。这一混,混得连名号都没了。唯有默默地用谁也掩盖不了的豆腥味,彰显自己的存在,撑起一餐饭,和关于黄豆的传说。不过,讲得再热闹,杂面毕竟是杂粮,当不了主食。比如杂面颗颗儿,现在多是在本地人开的火锅店里,以小吃的身份,给大鱼大肉后的食客解油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