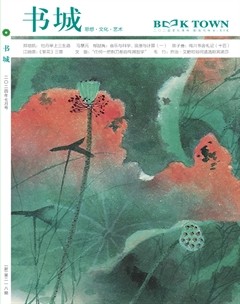帕尔马的《秘鲁传说》说,古代秘鲁的利马城里有所谓的“哭丧婆”,是一群满脸皱纹、比穷人身上的虱子還干瘪的老太婆。她们的职业是抽噎哭泣,大把大把地甩眼泪。这些人都像巫婆和老鸨一样,老得不能再老,丑得不能再丑。凡能留下一笔可供办起一场体面丧事的财产的人寿终正寝,遗嘱执行人和死者眷属便会走街串巷,寻访最有名的哭丧婆,由她再去雇佣陪她一起哭丧的伙伴。报酬是首席哭丧婆四个比索,陪哭者每人两个比索。当办丧人装出一副慷慨大方的样子,除正价外多给几个小钱时,哭丧婆们也得有点额外举动。所谓额外举动,就是一边号哭一边顿足捶胸,像发羊痫风一样抽搐和揪头发。她们和那些手拿蜡烛前去吊丧的所谓“穷光蛋”一起,在教堂门口等着遗体抬进抬出,尽情发泄她们那出卖的悲痛。要说利马有什么有利可图的职业,那就是受雇哭丧婆这一行了。在所有哭丧婆里,有一个高级哭丧婆,她是这类人中的至高无上者,只有为总督、大主教或最显贵人物举行丧礼,她才屈尊到场。她与众不同,雅号叫“圣星期五的受雇哭丧婆”。所以才有了这种说法:“某某先生的葬礼真是登峰造极了。你听啊亲爱的,连圣星期五的受雇哭丧婆都光临教堂门口了。”(《圣星期五的受雇哭丧婆》)
“哭丧婆”当然不仅仅是古代才有,马尔克斯也写过现代的“哭丧婆”。“哭丧—这项活动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又派生出许多有趣而又荒唐的细小区别—在拉谢尔佩镇土生土长的居民心目中,是一种职业,它不应当由死者的家人从事,而是要交给一个女人,一个无论从素质上还是从经验上都堪称专业的哭丧婆。”“哭丧婆们不是来哭死人的,而是来向来宾当中的显贵人物致敬的。当人们发现某个因为富甲一方而被当成有特殊贡献的重要人物将要登场,便会有人通知值班的哭丧婆。接下来的情节就非常有戏剧性了……哭丧婆双臂高举,脸戏剧性地抽搐着准备放声大哭。随着一声长长的呼啸,刚刚到来的人听到了整个故事—听到了死者的走运时光,也听到了他的倒霉岁月,听到了他的优点,也听到了他的缺点,还有他的快乐、他的痛苦;而故事的主人公此时正仰面朝天躺在一个角落里渐渐腐烂,身边不是猪就是鸡,身下垫着两块木板。”(《拉谢尔佩镇的奇异偶像崇拜》)秘鲁在太平洋沿岸,这里是大西洋沿岸,可见得在两大洋之间的美洲都有这一行当。在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写到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临终时,想象人们会雇一些哭丧婆来哭他,可见墨西哥也有哭丧婆这一行当。
之所以会有这一行当,无非是因为有需要。死人是必须有人哭的,否则显得活人没感情,更显得死人没面子。尤其是死者的亲人,特别是死者的儿女,不哭更是大逆不道,有违社会良善风俗。也就是说,哭有两种基本的功能,一种是满足感情的需要,一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哭丧婆”满足的是后一种需要。
哭的两种基本功能,在《红楼梦》里的贾珍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