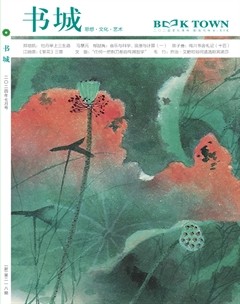尘埃已在表面落定: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花月杀手》获得二○二三年度奥斯卡十项提名,最终颗粒无收,让人大跌眼镜。
故事说的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为黑暗、肮脏的谋杀戏码”:一个世纪前,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奥赛奇印第安族群变成了最容易遭到谋杀的对象,数十起谋杀成为悬案,唯有莫莉一家人的案件水落石出,主犯被绳之以法。
从文本到电影:编剧很懂影帝
电影原著是二○一七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花月杀手:奥塞奇谋杀案和联邦调查局的诞生》(下文简称《花》),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获得了埃德加·爱伦·坡最佳真实犯罪小说奖。作者大卫·格雷恩(David Grann)是美国非虚构写作领域的标杆性人物,畅销榜上的红人,特别会选吸睛又刺激的题材。他擅长扣人心弦的编年史和犯罪故事,钟爱探险家和杀手的故事,热衷于描写阴谋和背叛,但他书写的故事都是确实发生过的史实。
相比之下,《花》具有格外深远的历史意义,小说一问世就迎来了七位数的翻拍版权竞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和J·J·艾布拉姆斯等人都曾接触过这个项目。格雷恩从二○一二年夏开始采访和搜集小说素材的工作,“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在学校时,从未在任何教科书中了解到这些谋杀案的介绍,仿佛这些罪行被从历史中彻底消除了。因此,当我误打误撞发现提及上述谋杀的文献后,便开始着手调查。自此,我便醉心于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填补联邦调查局侦破工作留下的空白”。
书名已充分表明本书的另一个重点落在“联邦调查局的诞生”上,相比于讲述奥赛奇谋杀案的第一部和第三部,第二部以探员汤姆·怀特为主角,详尽描述了艰辛的办案过程,以及本案大获成功对胡佛创建联邦调查局的意义所在。因为奥赛奇族人深知自身所在的郡县已被白人恶势力全面掌控,无法伸张正义,便在一九二三年要求联邦政府派遣与本州或本郡毫无瓜葛的探员来调查系列谋杀案。怀特直捣虎穴,很快就意识到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官方机构都是共犯,让奥赛奇印第安人的处境更糟糕,无处申冤,一系列投毒致死事件也表明医药系统同样不可信任;白人设定了不公正的监管政策,导致奥赛奇族的财产监护人或执行人大多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白人士绅,为这些人侵吞侵占行为提供帮助、打掩护的执法人员、检察官以及法官也属一丘之貉,甚至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侵占财产的执行人或监护人—堂而皇之地把非法掠夺“合法化”。侦破案件并不难,打破这套规则才难。怀特破案后,绝望地发现,到了庭审阶段,法官竟会找寻、编造各种理由解散陪审团,导致被告凶犯无法被定罪,比如指控布赖恩·伯克哈特谋杀安娜·布朗的案件审理就以陪审团悬而未决宣布告终,白白耗费了怀特和调查局三年多的时间。但对于胡佛来说,只要有一起奥赛奇谋杀案宣告成功侦破,他领导的现代意义上的调查局就有了能炫耀的政绩,足以证明: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执法力量是多么重要。事实上,此后生发出的不只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还有对美国政治有重大意义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怀特的人生故事跌宕起伏。他性格沉稳,心地善良,探此案时大胆启用卧底,办案手法可圈可点。更具戏剧性的是,他在本案了结后主动离职,不再当胡佛的金牌探员,因为他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像父亲那样监管监狱,而本案的两大主犯—欧内斯特·伯克哈特、威廉·黑尔—恰恰被关进了他监管的监狱。“当怀特在不同囚室间巡视时,仿佛是在记忆的坟墓里穿行,因为可以看到曾经在自己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人,他们的眼神在铁栏后飘忽张望,他们汗流浃背。他看到了黑尔及拉姆齐,他遇到了艾尔·斯宾塞匪帮的歹徒,他见到了丑闻频出的哈定总统执政期间因为收受贿赂被判入狱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前负责人……怀特还遭遇到杀害自己兄长达德利的两名亡命徒。”这一段读来就像一个残酷又隐忍的长镜头,甚至像一个时代的缩影。
怀特的人设非常饱满,在本案之前、之后的故事都值得一读。按理说,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完全可以把他作为男一号,有充足的正能量,能让人热血澎湃。据说,第一稿就只改编了原著的第二部分。斯科塞斯拿到第一稿剧本后,立刻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来演怀特。
然而,迪卡普里奥不肯,铁了心要演欧内斯特!于是,编剧写了第二稿,怀特成为两小时后才出场的配角,调查局的故事隐入背景,不再成为重点,但最终得到了原著作者格雷恩的盛赞,因为“忠于历史比忠于原著更重要”。
值得一说的是,该剧编剧是鼎鼎大名的埃里克·罗思(Eric Roth),曾写过《阿甘正传》《慕尼黑》《沙丘》《一个明星的诞生》等名作的剧本。这是一次很有趣的改编,影帝的钦定决定了一个微妙的配角成为主角,也解决了斯科塞斯有过的困惑—汤姆·怀特太像救世主了,会让这部电影显得毫无悬念。怀特是白人,但在这部电影里,白人不应该既是救世主,又是杀人犯。于是,在原著中看似漠然、顺从乃至矛盾的欧内斯特给出了充分的演绎空间。迪卡普里奥显然对自己的演技很有把握,很想演出这个白人身上“平庸的恶”。无奈不少挑剔的观众觉得他这次的演出主要是靠下巴和嘴,表情单一,用力过度。不过,格雷恩忽略了表情管理之类的细节,表扬得一语中的:“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拍一些低俗的犯罪片……欧内斯特·伯克哈特确实是更复杂但更关键的人物之一。他不是反社会者。我所做的所有采访和来往信件都清楚表明他对莫莉有真挚的感情。但正如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他渐渐深陷其中,成为这些谋杀案的同谋。”
欧内斯特是主犯黑尔的外甥,在原著中的存在感并不算太強,因为原著中的罪案故事是从受害人莫莉写起的,欧内斯特出场仅两页就和她结婚了。但欧内斯特是电影里贯穿主线的主角,故事就是从他退伍后投奔舅舅黑尔开始的,原著中仅以一句带过的学习奥赛奇语的介绍被扩展为黑尔对他的刻意调教—年轻人聆听长辈教诲的时候还会露出憨憨的表情,对黑尔多年来处心积虑谋财害命的内情一无所知。电影在欧内斯特和莫莉相恋、结婚的情节中不疾不徐地展开,但气氛始终紧张,因为很有节奏地穿插了数个印第安人被谋杀的场景,且都以冷血无情的全景镜头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