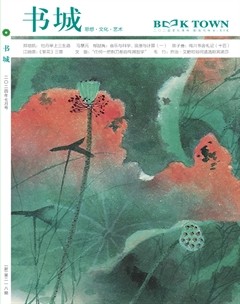在尼采(1844-1900)去世一百二十四年后的今天,现代人仍在不断重访他的人生、他的哲学乃至他的疯狂。他的故事被电影演绎,他的脸出现在手机壳和帆布袋上,他的格言化作歌词进入流行金曲传唱于悠悠众口。在大众文化造神运动的狂潮当中,我们还能辨认出那个曾经寂寂无名的哲学家、那个半盲的病退教授、那个孤独得要靠麻醉剂才能入睡的失恋者吗?《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苏·普里多著,刘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正是一次恰逢其时的辨认。在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中,尼采无疑是一个特别需要语境的思想者。要理解他,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乃至其人际关系和生存境遇。《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恰提供了这样一种语境。传记作者苏·普里多(Sue Prideaux)对于瓦格纳、科西玛、布克哈特、莎乐美、保罗·雷、伊丽莎白、尼采父母乃至路德维希二世等人物的精细刻画,有效地勾勒出尼采所处的生命境遇,为他的作品提供了鲜活的时代注脚。普里多仿佛一位珠宝大师,为读者打造了一顶宝光流溢的冠冕,为了烘托中心最璀璨的那枚宝石,她精心挑选并打磨了周边数枚较小的宝石,并镶嵌了数之不尽的碎钻。
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阅读并谈论尼采?这或许首先是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尼采所提出的问题当中:上帝死后,我们应该拿宗教的废墟怎么办?就此完全投身于科学和达尔文主义是可行的吗?由神性世界承诺给人间的道德架构此后又该建立在哪一片地基之上?生而为人的意义是否依然成立?为自己而不是为神寻求意义,是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如果说生命的意义仍然存在的话,人应当如何获取它?一旦神被抹消,还有谁在爱着世人呢?世人敢于爱自己吗?世人知道该如何爱自己吗?平凡如你我,是否可以成為超人?如果是的话,我们应当怎么做……以上诸般,正是尼采留给我们的问题。而答案,则纯然是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需要每个人以身入局,赤诚以求。
更直接一点来看,尼采的魅力恐怕还在于,他为他的天才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这使得世人对他的感受难免微妙而复杂。命运的慷慨馈赠里埋藏着终将兑现的苦涩,暴风骤雨般摧枯拉朽的智慧中潜伏着莫大的遗憾。敬仰他?当然。但这敬仰中掺杂着些许迟疑,他的疯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归因于他的哲学?怜悯他?有一点。但怜悯恰恰是被尼采所鄙弃的弱者道德观,一种危险的病态。并且事实上,在他的天才与狂想面前,我们又暗地里担心,谁也不配怜悯这样一个强悍而高傲的灵魂。
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尼采在都灵街头抱着一匹老马的脖子陷入疯狂,时年四十四岁。如果不是他的房东认出了他,或许尼采已被意大利疯人院的迷宫吞没。此后直到去世的十一年间,他日益丧失理性,思考和语言的能力逐渐离开了他,就像叶片离开冬天的树。“酒神”曾是他用以震撼世人的第一个概念,但还不仅如此,酒神概念在他一生的思考中被逐渐发展为对于生命意志的表征,并最终成为尼采的毕生追求,以及他最为贴切的自我认同。在《看哪这人》这部自传中,尼采以一句“狄俄尼索斯反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作为全书的结尾,而在理性逐渐失控的日子里,他在给亲友的信件末尾曾频繁地将自己署名为“狄俄尼索斯”。
在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以日神和酒神为两种对立的基本文化力量命名,并认为正是此二者的辩证交融成就了古希腊悲剧。
日神(阿波罗)掌管造型艺术,寓示着光明、清晰、秩序、克制、可控性和始终在场的自我审视。造型艺术对于控制力的高度要求,也许可以用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圣殇》作一番旁证。米氏一生中四次雕塑《圣殇》,第一次是来自梵蒂冈的订单,那时他年仅二十三岁,身强力壮,拥有对自身技艺和大理石的强大控制力。在那件作品中,圣母和耶稣的皮肤都经过小羊皮和天鹅绒的打磨,呈现出柔润、光洁的质感,完美得逼近神迹。这也是米开朗琪罗一生中唯一刻上自己名字的作品,至今仍被供奉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相比之下,第四尊《圣殇》则创作于米氏八十八岁高龄,据说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仍在挥动锤子进行最后的尝试。但它始终没有完成,人物面目模糊,而且存在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谬误。这件未完成的作品现存于米兰斯福尔扎古堡,向我们展示着大师无可奈何的衰老。由是可见,在造型艺术领域,在理性之光务必持续照临的领域,在必须让锤子与石头硬碰硬的领域,艺术家控制力的强弱是具有决定性的。
酒神(狄俄尼索斯)掌管以音乐、舞蹈为代表的非造型艺术,寓示着幽暗、迷醉、狂乱、激越、失控感和全然忘我的投入。酒神状态意味着抹消一切边界,其中包含着三个层面的边界:人与自然彼此和解,双方从对抗关系中解脱出来,人感到与自然浑然一体,大地也脱离了被奴役、被驱使的状态,献上它丰盛的产出;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失效了,在爱欲的迷醉或者大众的迷狂中,人们不由自主地结成了更高、更超越的共同体;人与自我的界限消弭了,意识向无意识敞开了大门,人甚至自认为神,进入了变幻莫测的状态,这时的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艺术品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德赛》中所描写的“塞壬的歌声”既是神话史诗的想象,也是对来自内在深渊的狂热召唤的一种隐喻。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致力于破除人们对于希腊文明的迷思和定见,指出它并不总是处于孩童般的天真和光明当中的,而有其残酷、卑劣、粗野、失控的必然面相,这黑暗的一面是无法与其光明面割裂开来的,“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尼采将德意志文明的精神定义为酒神式的,并且把植根于日耳曼神话的瓦格纳歌剧高蹈为酒神与日神的辩证重聚。这样的观点和论述直接导致《悲剧的诞生》被学术界狠狠撇在了角落。笼罩着这部作品的主要是漠视,偶尔出现尖锐的抨击,认为该书完全是胡说八道,尼采则是语言学界的耻辱。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八百本《悲剧的诞生》只卖出了六百二十五本,而这已经是尼采发疯之前所见证过的最好销量。只有少数从属于路德维希国王和瓦格纳社交圈的人士,发来了不着边际的溢美之词。至于瓦格纳本人,显然对这本书赞誉有加,不仅因为尼采将该书题献给了他,还因为这本书几乎是在对他所从事的歌剧事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背书。更重要的是,日神之梦与酒神之醉,从这一对彼此矛盾又不断纠缠的概念中瓦格纳可以看到叔本华哲学里“表象”和“意志”的影子。而叔本华恰恰是把尼采和瓦格纳的精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颗纽扣。
从少年时代起,尼采似乎就很容易被二元对立的概念吸引。
十二岁那年,尼采无法忍受圣三位一体的理论,于是将其中的“圣灵”置换为“圣魔”,理由是上帝为了能够思考其自身,必须也能思考其对立面,因此也必须创造出其对立面。我们可以发现,如何解释那些必然存在的黑暗与邪恶,如何处理基督教(或者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中的全能至善神悖论,这样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