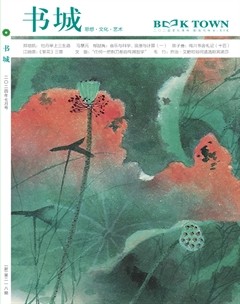一八四三年,二十四岁的玛丽·安·伊万斯第一次读到斯宾诺莎的作品时,沉寂近两百年的斯宾诺莎哲学在英国正处于被重新发现的风口浪尖上。(按,乔治·艾略特本名玛丽·安妮·伊万斯,直到1856年创作和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时,她才采用乔治·艾略特为笔名。22岁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玛丽·安·伊万斯,1851年来到伦敦后改名玛丽安·伊万斯。本文将按照她当时的不同名字来称呼。)按照通行的看法,斯宾诺莎写作的那些“在地狱之中锻造的书籍”本应不会与尼采笔下的“道德主义小女人”乔治·艾略特产生任何关联,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却是,在成为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之前,哲学女青年玛丽安·伊万斯曾经有过一段长期阅读与翻译斯宾诺莎的往事,或者更确切地说,翻译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构成了《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杂志编辑和撰稿人玛丽安·伊万斯投身小说写作之前所做的最后一项长期工作。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论题。要知道在维多利亚時代,公开谈论与研究被打上“无神论”与“异端邪说”烙印的斯宾诺莎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社会禁忌。那个时代,斯宾诺莎的著作长期以来仅在小范围的智识圈层流传,作为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独立女性玛丽安·伊万斯,为何年纪轻轻就接触到了斯宾诺莎的作品?这个问题涉及斯宾诺莎哲学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接受史,以及作为英国第一批传播斯宾诺莎学说的知识分子之一的乔治·艾略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一
众所周知,以“caute”(谨慎)为座右铭的斯宾诺莎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仅有一部冠名《依据几何学证明勒内·笛卡尔〈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Renati Descartes prinipiorum Philosophioe pars prima et secunda demonstrata,1663)的作品以实名发表,而其一六七五年完成的《伦理学》(Ethica)曾在出版前被叫停,只在一个有限的小型朋友圈之内传看。一六七七年二月斯宾诺莎去世后,才由其友人编订出版。一六七七年九月四日,斯宾诺莎曾经的熟人、宗教改宗者尼古拉·斯坦诺(Nicolaus Stenonus)向罗马及普世宗教裁判所首席圣部(Suprem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Roman and Universal Inquisition)检举了斯宾诺莎,认为其哲学具有异端危险的倾向,此后斯宾诺莎的作品逐步被梵蒂冈天主教会列入了“禁书名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由此很长时间内,人们只能通过斯宾诺莎的敌人为了攻击其思想而转述的只字片语来了解斯宾诺莎的观点,以致斯宾诺莎思想不仅缺乏传布,而且还极易遭到歪曲。
斯宾诺莎的生平遭遇也同样如此,只有两部严重失之偏颇的斯宾诺莎传记是在他死后不久写作的:《斯宾诺莎先生的生平》(La vie de Monsieur Benoît de Spinosa)可能是斯宾诺莎的朋友让·马克西姆廉·卢卡斯(Jean Maximilien Lucas)在一六七八年完成,直到一七一九年才出版;一七○五年,路德宗的德国牧师约翰·柯勒鲁斯(Johannes Colerus)出版了《论耶稣基督从死亡中真正复活,反对斯宾诺莎及其追随者:连同从其遗作和仍然活着的值得信赖的人的口头证词汇编而来的这位哲学家的精确传记》。柯勒鲁斯并不认识斯宾诺莎,他的资料主要来自斯宾诺莎生前最后租住住宅的房东夫妇,他的传记也带着明确反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先入之见。这部传记要比卢卡斯的传记早出版十四年,而卢卡斯的传记出版后旋即遭禁,只有少数几本被允许在特定读者群体中流通,以至于在后世人们眼中,柯勒鲁斯的传记俨然成了关于斯宾诺莎生平的权威版本,而柯勒鲁斯本人甚至似乎从未听说过卢卡斯版传记的存在。
围绕斯宾诺莎哲学的批评之声,自从一六七○年《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以虚构的出版商和错误的出版地点匿名出版之后不久便不绝于耳,这些批评以及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构成了斯宾诺莎生前推迟发表《伦理学》的充足理由。不过斯宾诺莎同时代批评者们的共识之一,就是极为小心地不把斯宾诺莎学说的全貌通过引文的方式呈现给公众,通过这种策略,他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有效地阻止了斯宾诺莎哲学的传播。可以认为,第一次向公众展示斯宾诺莎学说梗概的著述是,一六九七年由法国胡格诺派学者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撰写的《历史和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中的一个简短而具有高度偏见的词条(尽管这个词条是这部辞典中最长的,但它显然远不足以概述斯宾诺莎),他把斯宾诺莎描述为“一个系统的无神论者”。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一项极为严重的指控,很长时间内主导着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