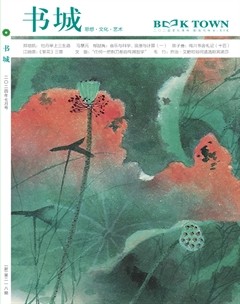月明云淡露华浓
“五一”期间奔赴了一趟苏州,为了观看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演出的经典版《玉簪记》。之前曾在网上看过岳美缇、张静娴二位演出的录像,及其他各团的演出版本。相比之下,唯有上昆这一演出版本的整编堪称绝妙,名之为“经典版”,十分恰当。
如今搬演传统昆剧,推广时最重演员,对文本的解读和剧本沿革的释讲,往往还不如对演员的介绍。殊不知昆曲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非仅仅是因为表演,它的历史、文学,包括曲辞、曲牌的艺术价值更为要紧。每逢演出,应为观众多多加强引导欣赏的功能。
《玉簪记》传奇是明代中晚期作家高濂的作品。自问世后,就其曲辞、宾白、场景和人物设定,向来疑议不少。兹举数例:
《玉簪》词多清俊。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经,纰缪甚矣。(明·吕天成《曲品》)
《玉簪》幽欢女贞观中,境无足取。惟着意填词,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贯词……(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玉簪记》之陈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禅堂打坐”,其曲云“从今孽债染缁衣”;禅堂、缁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诸如此类者,不能枚举。(清·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宾白第四》)
此记传唱四百余年矣,顾其中情节颇有可议者。……至于用韵之夹杂,句读之舛误,更无论矣。编制传奇,首重结构,词藻其次也。记中《寄弄》《耽思》诸折,文彩固自可观,而律以韵律,则不可为训,顾能盛传于世,深可异也。(吴梅《曲选》)
以上指摘,多针对“扮尼讲经”。确实,《玉簪记》场景设于女贞观,人物为道姑,此为道家,在传奇本中却有“谈经”“念弥陀”,确属混沌。
大概因为这一缘由,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纳书楹曲谱》起,到二十世纪中叶《春雪阁曲谱》《六也曲谱》《集成曲谱》《与众曲谱》诸曲谱中的《玉簪记》唱演本,对剧情、关目已做了很大的筛减和更名。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书城》2024年7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